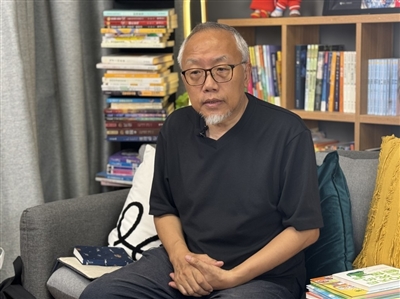
■受访者:毛丹青(旅日作家、商人、讲师、译者)
□采访者:孟丽媛 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毛丹青有着多重身份,旅日作家、商人、讲师、译者等,对身边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好奇与探索之心;多年来的研究,他深谙中日文化的同与异,通过写作、翻译、出版等,为中日文化间的交流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脚印。
毛丹青爱散步。在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他经常从新宿步行到东京车站,边走边看,触景生情,温习昔日时光。2024年,他再一次回到北京,行走在街头,突然回忆起50多年前在街道上看到缓步穿行的驼队,仿佛听到那一声声驼铃,还在耳边震动。
在日坛公园旁边,有一条普通的南北向街道,就是老北京人经常提到的“豫王坟”。300多年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15个儿子多铎去世后曾葬在这里。听说埋尸骨的地方会有闪着光的金牙,小时候的毛丹青就经常和玩伴们拿着小铲子去刨;再往东的位置叫灵通观,有几条长长的铁轨,他和小伙伴们就把钉子放在火车轨道上,等待路过的火车压过钉子,让钉子变成他们心心念念的“钉刀”。
那些趣事都在毛丹青的手账本上记录得独特又有趣,手账本上所有的插画没用铅笔反复描摹、修改,而是用圆珠笔一笔勾成,就如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一样,简单、明朗又热烈。听着毛丹青缓缓道来生活的见解和乐趣,仿佛已然和他置身于同一个充满松弛感的生活空间。
这么多年来,他每次回北京都有不同感受,这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形成的,而与亲人之间的纽带是人的思念,这是唯一且不可复制的。今年8月底,本报记者对毛丹青进行了采访,请他讲述生活与写作。
□你觉得在目前快节奏的生活中,怎么给生活做减法?
■我觉得在当代生活减法应该大于加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被设定好的。比如日本,女性寿命平均83岁,男性寿命平均79岁。在我们被设定好的航程当中,如果你提前透支得太多,比如年轻时吃喝玩乐,做一些无用功,那么透支的这部分到了老的时候就会反弹得很厉害,考虑长线只有做减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低欲”,“迎终低欲”即降低你的欲望,迎接你的死亡。终是终止的终,迎是欢迎的迎,我觉得这个思维非常好,我在接力出版社做的几个漫画绘本都是这个道理,这种想法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带给绘本主人公的,不是说一定要追逐什么。我很多年轻的学生都碰到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时间太紧张了,什么时候能够缓慢一点。我就一直在讲,低欲非常重要,规划时间长一点,如果太追逐眼前的东西,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或者很疲劳。
还有远离虚拟,接近现实。我们现在网上看的短视频,包括一些快节奏东西,它都是虚拟的、被大家消化过的、被议程设置过、被流量冲击过的。现实的东西,你到公园里感受一些空气、看到一些阳光,哪怕旁边走过一个老人都会有一种关怀,这对你的肢体、语言的叙述和我们小小的手掌握着的屏幕上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60多岁了,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现实大于虚拟,我们经过了现实逐渐走到虚拟当中,当虚拟要吞并现实时,我们年少时的记忆就会打破虚拟世界,回到这种点对点的现实当中,内心就会比较稳。我们叫生活如水、至暖至温至荣。
□2002年,诺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访华时拜访中国作家莫言,你全程翻译,在与两位诺奖作家的接触中,你觉得他俩在文学创作上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次对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非常巧,2002年《朝日新闻》一个编辑跟我说,他在编我的书的同时也在编大江健三郎的一本书,那时我还不认识大江,但我知道他已经拿到诺奖了。编辑对我说大江特别欣赏中国的一位作家叫莫言,莫言是我很好的朋友,认识莫言30多年了。当时大江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很震撼,他说他读过莫言的《秋水》,这个小说写的是发洪水时村落里的一个故事。大江提到《秋水》里面的一段话说:洪水犹如马头一样,像奔腾的马冲上来。他搞不清楚,说洪水像马头是它的高度还是它的样子还是其他什么,能够这么具象。我说你这么喜欢看的话,我们干脆去找他,你亲自去看一看。大江就很愿意,这种文学的力量可以排除所有的东西。
后来我们到了莫言的老家高密,真的到《秋水》描写的地方,结果到了之后什么也没有,干枯的河都没有,全是假的。所以文学对谈并不是为了交流而交流,而是为了他们的某一个点,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你要站在作家的立场上去分析它。不同的作家感觉不同,有的听觉比较强,有的嗅觉比较强,有的视觉比较强。比如说余华和苏童,苏童有一个很奇特的功能,他的嗅觉特别强,他说可以闻出各种各样的气味。2006年,余华与我第一次到东京时,他就专门找楼与楼之间的树,高楼大厦,中间,会在小小的一条路径上面长出几棵树,他就担心绿树的树枝长出来以后,怎么能够和大楼抗争。他在《活着》里有一段类似的描写,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描述,就和刚才说的《秋水》里洪水像马头的道理是一样的,懂文学的人就会进入它。
你要是不懂文学,你只会说他怎么有名,小说怎么厉害,票房怎么好,其实都不是。真正作家能够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往往来源于很多细节,这也是我常年最追崇、最看好的部分。
□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的区别在哪里?两国作者们创作的区别在哪里?
■有区别的原因是语言限制,语言是牢笼,语言不是无限制的。像莫言的文字在这方面就有点泥沙俱下;相比之下,余华的文字就懂得雕琢,中学生都可以看得懂;苏童的语言趣味感非常强,因为语言有伸缩性。日语完全不是这样的,它是非常蹊跷的。川端康成的《雪国》一开篇就震惊世界,“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是什么东西穿过隧道他不写。
作家之间的不同,很多人说是思想、经历等不同,我觉得每位作家本身的语言也在控制他。大江健三郎曾讲过,语言来源于哪里?来源于饥饿,当你没有温饱的时候,它有一种东西可以填补你的温饱;想象力从哪里来?就是从饥饿而来。莫言说过,放牛时饿得要命,就躺在地上看天上飞着的白云,想象着白云变成馒头掉到他嘴里,进入他的肚皮里,然后排泄出来——云变成馒头进入他的身体。大江健三郎也有同样的思维,但他的主体是树,在一个森林里面,有落叶从树上飘落,然后变成铜锣烧,跑到他的肠胃里蠕动。
这是文学高峰的对话,所以作家和作家的不同,最大的区别是语言。有关的讨论很少,是因为对语言了解的人很少,语法是无法解释的,它很神秘。所以语言不是广场,语言是牢笼。
□怎样看待“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我们也叫夕阳红产业,它给年轻人一个新的方向,告诉大家有这样的阅读群体,从出版角度来说,给老人定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老人购买力非常强,他们有时间、有钱、身体动不了、读书很厉害,现在已经有很多专门为老人写故事的作家,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点。比如说,绘本卖得好的一个原因是老人读绘本。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就变成了医院的消费品,要付很多钱去挽救苟延残喘的部分;怎样提高生命质量,就是给他不断提供精神食粮。所以现在做绘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仅是给3~5岁、5~8岁、8~12岁的儿童分阶段按照多少页来算,它是程序化的;老年绘本不是页数的问题,而更看重整个故事氛围。
□中日青年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否一样?
■我的班上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学生,我经常会促成学生之间的交流。相比之下,中国学生非常有志向,都很“猛”,格局和日本学生完全不一样。因为日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日本学生不用太多努力就可以得到他的份额,在生活中他们没有焦灼感。我班上所有的日本学生都可以找到工作,就业率高到可怕的程度。但是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或在日本生活如鱼得水的人,他们基本上都走向自己创业。当然也可能是因人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