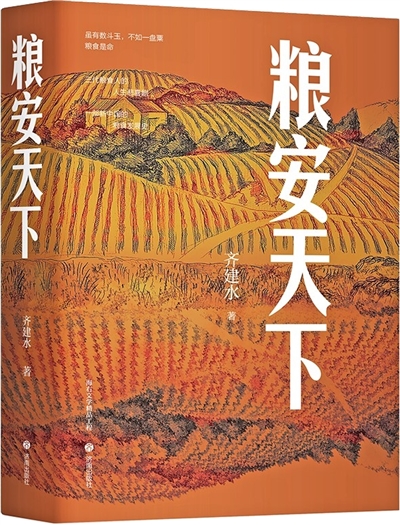○逄春阶
《粮安天下》是一部中国当代粮食管理史的形象化表达之书,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塑造了粮食人的群像,写出了他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展现了朴素的人性之美。
我想说的一点是,《粮安天下》具有超越血缘关系的世俗性表达。一是陈良石视陈满囤如己出,对继子关爱有加。当陈满囤执意要跟秀月闹离婚劝解不成时,陈良石气得不行,陈满囤说:“你不是俺亲爹,说话都是向着别人,从来不为俺着想!离不离婚是俺个人的事,你们谁也别管。”这话太伤人心了,刀子一般扎心。小说这样写:“‘混账!’陈良石身子一哆嗦,心仿佛被一支箭射穿了,流出血来。他愤怒地举起了巴掌,然而举起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尹巧凤一听儿子说出了这样的话,大为震惊,指着满囤愤恨地骂道:‘你这死孩子!说什么话!’”满囤被枪毙以后,收尸,“陈良石一看满囤的尸体扭曲地躺在地上,忍不住大泪横飞,叫一声‘儿啊’然后哇地一声哭了,接着想扑上去。”“陈良石痛苦得咧咧嘴,让人从不远的河边提来一桶水,紧咬着嘴唇为儿子擦脸,擦身体……”他检讨自己在满囤的成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他的死产生了什么影响。他想不明白,自己在满囤身上种的都是爱啊,是想让他有饭吃,有衣穿,有好日子过,有个好前程啊,怎么到头来收获的却是这样的结果?这就是超越了血缘的亲情。
我们做父母的,是真爱子女,没有掺水的。这点不能否认,但是怎么就觉得彼此是拧着的呢?问题大多出在父母身上。爱一旦变成溺爱,就出问题了。这是《粮安天下》的深刻处,也就是写出了世俗性、人间性,陈良石是有地位有权力的人,权力对人异化了。崇尚权力是人性的本能,于是飞速发展的时代,异化也在飞速,因为权力所能覆盖的世界太广阔了。还有,它的残酷在于父母往往是以爱的名义。“爱”这个词在亲情中有着无法厘清的边界,它特别容易模糊是非颠倒黑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大于理。如果其中再附着着价值观的移位,对下一代的迫害就更是雪上加霜。小说写出了生活的苦涩。
超越血缘关系的第二个是陈良石和尹巧凤接纳了冯兰英和杨中吉的孩子陈满仓。第三个是乔秀月接纳了满囤和高爱玲捡来的孩子金谷。这种超越血缘的大爱,最打动人心。陈良石身边的孩子,没有一个跟他有血缘关系,其感悟是:对于抚养孩子,所有的苦都不是真苦,因为这些苦中孕育着希望。
超越血缘的人间大爱,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思想,墨家“兼爱非攻”的无差别关怀理念,宋代张载“民胞物与”的天地情怀,共同构筑起这种大爱的精神内核。这种美德在历史长河中体现为邻里互助的义庄制度、收容孤幼的慈幼传统,在当代则升华为现代公益精神。它既是对“仁者爱人”传统价值的赓续,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文明突破血缘界限、追求普遍关怀的道德高度。
诗人欧阳江河在博鳌文学论坛上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怎么写的问题,是怎么活的问题,活多深,才会写多深。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越来越体会到写作的深度到达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命运深度。《粮安天下》沉甸甸的,它的世俗性、人间性,值得肯定。
读完小说,我脑子里想到了几个词:珍惜粮食,平视人、善待人、理解人、尊重人,而不是蔑视人、藐视人、轻视人、忽视人,包括对自己的亲生儿女,是从骨子里的平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第十二届山东省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