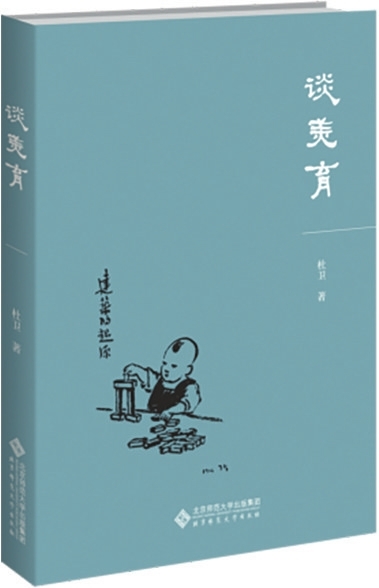
■周 粟
1932年,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提出“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的美育构想;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光阴流转,如今的美育研究已枝繁叶茂。2025年,杜卫教授在最新出版的《谈美育》中写道,朱光潜先生的《谈美》,“虽然谈的是美学,实质上篇篇紧扣美育”。《谈美育》正是在向朱光潜学习,从“谈美”到“谈美育”,由“照着讲”进而“接着讲”。掩卷方觉,《谈美育》确以温暖而灵动的“漫谈式”语言,将“什么是美育”深入浅出地讲透了。
如王国维所言,美育的作用恰在于“无用之用”。杜卫教授在《谈美育》中进一步剖释,“无用之用”中,前一个“用”指饱食暖衣、功名利禄的物质世俗利益,后一个“用”则指部分消除个人利害计较、提升精神境界的高尚人格培育。尽管看似“漫谈”,《谈美育》读来却给人一气呵成的阅读“美感”,这是因为在全书13篇文字内里,暗含着一条串珠式结构——每篇都紧扣着“无用之用”这一美育主旨。
从谋篇结构看,《谈美育》实现了对美育底层逻辑的清晰拆解,不仅以“无用之用”的超功利性,串联起对美育历史、特征、目标、功能与方法的生动讲解,更以轻松通透的文字功力,呈现出美育与德育、艺术教育、文学教育、爱的教育、审美趣味、教师素养间的深度关联。最终这些美育的不同剖面“万取一收”,共同指向作者基于40余年研究经验,凝练出的“美育是基于审美经验的人文教育”这一核心观点。
从写法风格看,全书始终围绕关乎美育的“真问题”展开漫谈,“漫”而不“散”,娓娓道来。例如,当下年轻人关注的是,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获得平静乃至幸福感。对此问题,《谈美育》运用“美育素养”和“审美经验”来谈。首先,美育的目标是发展人的审美素养,而具有审美素养的人,更易从自然和优秀作品中获得情感慰藉与精神提振,得以在学校学习与职场竞争中获得内在的平静丰盈,于纷繁世俗生活中形成崭新的生命体验。进一步看,人们惯常理解中的“美育就是用‘美’教学生去认识和感受美”,实际是一种误解:20世纪以来,美学研究的核心其实并非“美”本身,而是“审美经验”;而美育的目标正是引导人们进入“审美经验状态”。那真正的“审美经验”又是什么?通俗理解看,审美经验即指人在欣赏自然美或欣赏、创作艺术美时的情感体验,而甚深的审美经验状态,恰如南朝画家宗炳谈到的“万趣融其神思”,本质上是在追求一种“畅神”的境界——这又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关于诗“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这一珍贵体验形成了内在互文。最后,杜卫教授借助中西艺术名家对“审美经验状态”的精深描述,指出那些具有审美经验的人,更容易跳出对个人功利性欲望的束缚,因为其真正触发了康德所说的“无利害性”的审美快感,已步入“无用之用”的美育至高境界。
从创新维度看,杜卫教授在《谈美育》中发掘并锚定了一些重要的美育“新概念”,令读者尤其是美育研究者灵犀骤启。如在阐述“丰厚感性”时,作者首先谈到欧洲的工业化文明使人远离自然,其中科学等理智的力量导致理性对人自身感性素养的压抑,造就了人性的分裂,进而激发了席勒美育思想的诞生——期望以偏于感性的审美和艺术恢复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使人重获“审美自由”。但是,单纯的感性往往缺乏深度和厚度,现代美育于是通过在感性素养中渗入人文内涵,实现美育浸润后人们“既具备感性的丰富性又具备理性的深刻性”这一中和状态,杜卫教授把这提炼命名为“丰厚感性”——“既有感性的丰富、生动、敏捷和活力,又有历史文化的蕴含和渗入;既有童心般的天真与幻想,又有哲理性的选择与判断”。《谈美育》进一步指出,人的情感体验能力是一种特殊的“理解力”,为将这种能力与逻辑思维中的理解力区分,不妨称其为体悟或者领悟能力。当具备“情感体悟力”时,作为主体的人便得以在想象中与审美对象形成情感移置,进而步入《毛诗序》描述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境界。由此,感性没有失去鲜活的生命活力,理性亦没有失去规范与秩序,感性生命与理性形式在“丰厚感性”中达到中和之美。而恰恰因为现代美育中的审美素养是一种包含理性因素的感性素养,所以美育培养的这种丰厚感性,最终必然通向“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的自然平和状态。
与此同时,《谈美育》对于当下极为重要的美育教师素养话题进行专篇讨论,深入谈到了美育教师应怎样“润物细无声”地实现“美育浸润”过程,应如何让学生真正形成内心对美的触动与感悟,最终得以进入由“为感而知”代替“为知而知”的高级美育阶段,从而激活学生的美感体验,积累他们的审美经验,实现对审美情趣、审美能力和审美观的培育目标。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全书穿插了多幅精美清晰的美育插图,如经授权呈现的丰子恺先生经典美育画作等,并且每幅图都配有作者精心写就的解读性文字,不仅为《谈美育》这本讲授“美”的著作增添了美学韵味,更有利于读者在品读“美育”的过程中涵养审美情致,感受美育这一“无用之用”的本真妙用。
(作者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