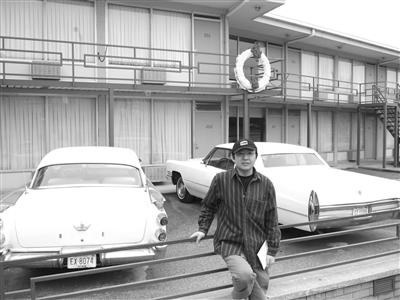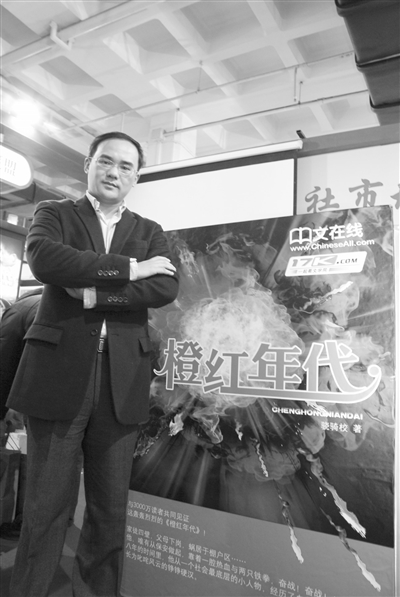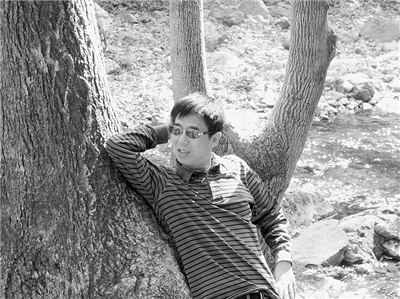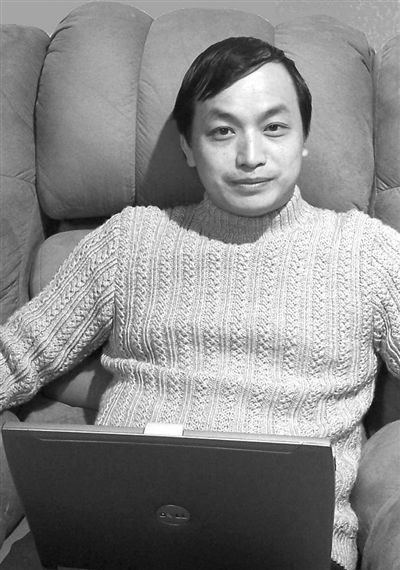在约稿的过程中,一些细节让我们特别感动: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韩石山老师在收到我们的约稿函的当天下午就给我们交回了稿子,而且前后3次对自己的文章进行反复、认真地修改。韩老师在回信中说,文中既是点名,又是道姓的,怕得罪人,所以要慎重。而远在美国的旅美作家李波老师也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2次修改——他们的慎重、认真、负责精神,颇难能可贵。——编者
事过境迁,犹记图书编辑知多少
○叶倾城(新锐女作家,著有《爱是一种修行》、《情感的第三条道路》等)
人到中年,大红大紫要看缘份,我但愿成为文坛常青树——常青,也就是永远不红。断断续续,也出了二三十本书,基本上,对于每一位我的编辑,我都怀着感恩之心:他们欣赏与错爱我,乐于冒着风险,编排一本又一本书。我自己常惶惶不安:万一卖不掉呢?他们都比我有信心。
我会感谢他,最初我并不曾想过要把情感信箱结集——这样一时一刻的东西,会有读者吗?是他主动与我联系,提供给我思路。我半信半疑,还是整了稿子给他。再拿回书稿的时候,我看到每一篇文稿都拟了妥贴而时尚的标题。我自己老土,也承认这些更亲切可爱。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靠谱、懂行、踏实,这样开始了合作,他换了几家公司,这一行业现在人如潮水,随着季风东南西北。他做书的认真,有时候抵不上设计的不认真或者结稿费的混乱。这不是他的错,图书行业是会乱中有治,还是洗心革面,我也说不上。
我也一直很喜欢她。她起先是我的读者,读研究生的时候写信给我,寄过一本她自己的书。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毕业了进了出版社,而:姐姐,出你的书是我的梦想。那时我正处在人生低潮,交完稿她问我书名,我随口答:“《痛》。”不然就“《痴》。”书当然不叫这名字,她倒是结结实实请我几次饭,我不肯说她大概也不好问,只是远兜远转地安慰——这份好意,我全心领。
想起他,是温馨的知己感。他从来不曾是我的责编。若干年前我崭露头角,同一本书贸贸然同时与几家出版社联系,他说很欣赏,但被另一家抢了先。他之后不再做文艺书,我们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但他一直赞叹我的才华——我?我真的有吗?在那个尚不曾有网络的时候,他看到好的书,港台的或者欧美的,会复印成一大包寄给我。他一直鼓励我写,我知道那是出于惜才之心,为此,我时常觉得愧对他。
总归会有让我觉得滋味复杂的。我的第一位编辑,那时我已经写了好几年,出书的念头笋子一样节节升高,我经常站在书店里看其他人的书——觉得他们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呀。总之,第一本书像头生子,往往难产。是他找上了我,我大喜过望,受宠若惊,把稿子排山倒海地全打印出来发给他。书还算满意,装帧设计都不错,但……他没与我签过合同,稿费、版税、印数,都没说。到最后,糊里糊涂给我几千块钱。
我到底是该感谢他巨眼识风尘,还是小小抱怨他欺负新人?承认后者微微让我不安,像张爱玲抱怨她的《西风梦》没得奖,“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那为什么还要写?就算是,忠实于自己的记忆吧。
编辑和作者其实是命运共同体
○李波(旅美作家,著有《我在北京有张床》、《狗眼看世界》等)
作者和编辑的关系颇为复杂,也颇为有趣。尽管作、编之间没任何竞争关系,却自始至终处于博弈。这种博弈关系,随着时间、双方资历等具体情况时而隐而不发,时而峥嵘毕露,时而和风细雨。
对于默默无名的作者,编辑处于绝对强势。即使八十高龄作者面对二十出头的小编辑,也如同小学生面对班主任,开口闭口“老师”。我不知道这习惯何时被引入出版界的。编辑称作者老师仅仅出于职业习惯,作者称编辑老师,发之肺腑——编辑对作品有生杀予夺之权,不敬也畏。我想即使功成名就的大作家,也逃不脱这经历——没被退过稿的作家好像没听说过。
在国内,出版被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三审制(censorship)严格而独特。任何出版物进印厂前,必过三个环节(所谓三审或终审),编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和作者见面的,往往都是一审编辑。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和质检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一审编辑通常和颜悦色,即使有意见,基本能放到桌面上说。作者大多自负,看作品就像看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顺眼,剪掉一“六指”割掉一“阑尾”都觉痛心。编辑呢,即使内心如火,也因长期业务锤炼而宁静如水,总能晓之以理达成妥协。但一旦要枪毙你的稿子,或要“动大手术”,通常会借用那只无形之手(二审或三审),不管是否是托词,作者都有和风车“作战”的无力感,不得不接受现实。最恶劣的编辑,就是拉稿时大包大揽,签了合同却无法履约,让你承担大量的时间成本。当时你可能很激愤,事后想,编辑也是无奈。当然,随着你的资历积累,话语权博弈的天平就会向你倾斜一些。
有一种情况是初审编辑出自内心喜欢你的作品,但无法通过那只无形却更有力的手,他会在和你共享沮丧之情之余想方设法:指点你怎么改,怎么绕圈子,怎么回避,怎么狗尾续貂般留一根光明的尾巴……如再失败,他会动用私人关系,推荐到别的社。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你都会对他很感激,说不定成为可以谈心,可以蹭饭,甚至可以借钱的好朋友。我就有这样的朋友,至今让我很感恩。
就跟任何产品出了问题质检员逃不脱关系一样,编辑和作者其实是命运共同体。编辑常自嘲为“为人作嫁衣的”,作者是穿嫁衣的。无论作嫁衣的还是穿嫁衣的,都是为了“新娘”漂亮。但如果编辑闭眼做衣,没准会做出“皇帝的新衣”来,“出风头”的是作者,担责的却是编辑。这样一想,任何对编辑的负面情感和认知都烟消云散了。
记忆中的编辑:血酬
○骁骑校(作家,著有《橙红年代》等)
写网络小说至今已有4年之久,之所以用“久”这个字,盖因网络小说历史不过10余年而已,而网络写手的职业寿命更是短暂到一两年乃至几个月,在4年的职业生涯中,免不了要和众多的读者、编辑发生交集,其中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责编血酬。
我原来是做电力自动化的,而血酬则是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种种机缘巧合,一个工程师和一个半路出家的律师因为一部名叫《铁器时代》的架空历史小说而在中文在线旗下17K小说网相识了,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是2007年。
和血酬的交流大多是在网络上,后来有一次我去上海见了他,魁梧的体型和刚猛的络腮胡子让我联想到董卓,但是一番高谈阔论之后,证明第一印象往往并不正确,董卓其实是个心思细腻、博学睿智的才子。
还记得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摆着辣酱瓶子和装满烟蒂的半截可乐罐,由此可以想象编辑们繁忙的工作状态,后来在北京的办公地点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后才知道,事实比想象的还要艰苦,饮食不规律,通宵熬夜是家常便饭,眼瞅着一个个年轻英俊的编辑陆续都变成了董卓,我明白他们是在以燃烧生命来创造价值。
众所周知,网络文学的门槛极低,每个编辑都要面对成百上千的作者和作品,工作量相当繁重,文学网站的商业化更加重这种劳动强度,但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无数优秀的网络小说在编辑的指导下实现了数字出版、实体出版,对于缓解社会压力,丰富人民群众文娱生活起到重大的作用。
4年过去了,我从一个默默无名的网文写手成长为在网络和实体出版都小有成就的作家,而血酬也从一个频道主编成长为整个网站的互联网部总编,成长总是令人欣喜的,而结识一个能伴随一生的挚友更是让人欣慰,记得年会的时候和血酬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谈网络文学的走向和发展,谈人生和理想,未来的道路还很长,我想又一个4年后,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会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以书为媒的“跨国婚姻”
○李国征(辽宁鞍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传国玉玺》、《浮沉》等)
一部作品走向市场,编辑是第一个“通关”审查官,于是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把编辑称作“媒人”。私底下我认为这个比喻很拙劣,因为它并不能准确反映编辑人员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劳动的神圣与崇高。
媒婆者,多是带有明显的营利目的,撮合成一桩婚事,她是要拿“抽头”的,为了这一点蝇头小利,哪怕明显不般配的一对男女,她也要夸得天花乱坠,至于当事人婚后是否幸福,全然不在她的考虑之中,甚至婚姻不成,她也要收口舌费、跑腿费;编辑则不然,相对于作者而言,他基本上属于幕后英雄、无名英雄。当一部作品在市场上走红时,很少有读者注意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是哪路神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时常为这些默默无闻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朋友们叫屈。
不过以书为媒成就婚姻,在我的出书经历中却是有过,而且还是“跨国婚姻”。
说起来是许多年前的事了。2004年10月,我的长篇历史小说《传国玉玺》完稿,经朋友介绍送给了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Josephine Leung女士几次与我电话联系,商讨修改与出版事宜,后来又把我介绍给日本东京光文出版社的於保秀子小姐。
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打到国外,对我而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所以也不能过于计较版税与发行数了。在由中文译成日文的过程中,秀子与我沟通颇多,彼此熟悉后,我得知这位毕业未久的大学高材生尚未婚配,于是在一次聊天中打趣道要给她作媒。不料这姑娘很大方地说,好啊,最好找一个会写小说的中国男人。语近玩笑,但我却很认真地思考起来。我熟悉的朋友在日本混生活的有很多,会写小说的固然没有,但说起责任心和对女人的体贴关爱,中国男人在日本人心目中声誉甚高,尤其为日本女人所青睐。于是我披沙拣金,终于选中一个在日本福冈读学位的旧同事。2005年春,我去了日本,当然主要是为办理出版手续一应事宜,同时也是去亲自当一回月下老人。秀子专程从东京飞来福冈,在一家名叫“樱岛料理”的小店,两人在我的引见下坐到一起,彼此竟然一见倾心,于是我作伐成功,而且在酒桌上,我的出版合同也签了字。本以为有了这层关系,在印数和版税上秀子会给我以关照,不料这日本妞儿原则得很,说社长没给她这方面的授权,所以她不能改变合同内容,虽然很感谢我为她介绍了一个未来的丈夫。
《传国玉玺》日文版在东京出版,秀子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我没能赶去参加婚礼,却将一本签了名的新书寄回日本,寄到一对新人手中。
编辑没眼光主要是没胸怀
○韩石山(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徐志摩传》、《谁红跟谁急》等)
中国的编辑,以服务的部门而论,可分为图书编辑、报刊编辑两大类,哪一类里,都有优秀的,也都有平庸的,甚至不称职的。相比较而言,图书编辑里的优秀之士,要多一些。不是什么精确的统计,全是一些个人的感受。
十几年前,我写散文还没有多大名气,不知为什么,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叫刘茁松的编辑,特别喜欢我的散文,总想为我出本散文集。他在古典文学编辑室,纵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种可能。机会终于来了。社里要出一套小说家散文丛书,所选对象都是当时的小说名家,他硬是说动了该丛书的编辑,挤进了我的一本,名叫《纸窗》。1998年1月出书。那年的春节,恰在1月下旬。为了让我能在春节那天看到新书,他腊月二十八赶到长沙郊县的印刷厂里,拿到第一本书,就在县城的邮局用特快寄出了——我接到书,正是除夕!
还是出散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老总张秀枫,则是另一种作法。那几年出散文集,兴一辑一辑地出,少则四本五本,多则八本十本,似乎没有少于四本的。他想为我出一本,又不想一辑里本数多了,结果是又找了两位作家,出了一辑三本,我的那本叫《真实是可怕的》。
外省的好说,难办的是本省。北京的出版社面向全国,似乎没有这样的难题,省里可就不一样了。都是朋友,给这个出了,那个常会找上门来。因此之故,省里的出版社,给本省作家出书,常是慎之又慎。2004年,书海出版社(山西)的老总杭海路,一次为我出过一套书,分别是《韩石山文学批评选》、《韩石山社会批评集》、《韩石山学术演讲录》。事先我说,老杭呀,你给我出了,万一别的朋友找上门来你咋办。老杭说,这是我的事你别管!
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堪。多年前,作家出版社的张水舟想出我一本文学批评集,应当说这是第一家要出我批评集的。我喜滋滋地编好送去,张先生加工送审,一个比他权力更大的人或是机构,经过一套程序,说这样的书没市场给否了。自己约的稿,弄了个这样的结果,张先生只好以实相告。我听了差点笑倒,也太缺乏智慧了,你可以说韩某人的作品没有人性,也比说没市场有些道理。此后几年间,我的文学批评集至少出了三种。同样是编辑,我总觉得,图书编辑似乎更需要眼光。而有没有眼光,端在有没有胸怀,有没有判断。
好编辑不仅仅是“锦上添花”
○云无心(科普作家,著有《吃的真相》等)
有一次跟“恐龙达人”邢立达聊起出书,他说“相对来说写书还好,出书中经常遇到各种烂事,太烦了”。我说:我还好,出了两本书,繁琐的事情都是小庄在打理,我只管写完文章就打酱油了。
在《吃的真相》自序里提到过,当初只是写博客打发时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称为“科普作家”,也没有想过要出版科普书籍。松鼠会出版了合集《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之后,姬十三就琢磨着为松鼠会的作者们出个人专辑。本来在《新发现》做得很好的小庄,为了寻找人生中“新的挑战”,离开上海来到了北京,建立了一个图书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的第一本书就是《吃的真相》。对于我来说,小庄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所有我不想管的事情,从挑选文章、分类编排、跟出版社谈判,到插图与封面设计、宣传推广等等,她都自己搞定了。我所作的,就是校对内容,以及在她准备好的合同上签名。直到有一天,她说“要开新书发布会了,你录一段视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而我,自我感觉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如果把“不添乱”当作一种好的“合作品质”的话。我从来相信处理那堆繁琐的事情非我所长,就不去指手画脚。到了《吃的真相2》,一切都轻车熟路,我基本上就是把文稿交给她(还有一些是她自己收集的),然后就等着书出来了。
一本书最后能有多大的影响,推广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我在国外,无法实地参加推广活动,基本上只能依靠文字媒体来推广。《吃的真相》是重庆出版社下属的华章同人做的,我跟他们的联系倒是不多。出版之后,有很多媒体做了介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营销编辑的努力。他们也介绍了许多媒体来做访谈,到后来也就有许多媒体自己找来了。他们把这些访谈和报道一一记录下来,据说总共有几百篇。作为一本追求科学严谨的科普书籍,在充斥着忽悠胡扯的“养生”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我自己的感受是“真不容易”。
小庄的图书工作室现在变成了“果壳阅读”,也在招兵买马。对于像我这样业余写作的人来说,有一个好的图书编辑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是“必须”的事情。否则,把精力花在打理自己不擅长不熟悉的事情上,就没时间写作了。
最痛苦的是被删改
○李师江(诗人、小说家,著有《逍遥游》、《福寿春》等)
在我出版几部书的过程中,与编辑交流过程中,最大的痛苦,就是被删改。我的小说几乎都有被删改过,改得让自己再读的时候,肝颤肝颤的,好像被割肉一样。
其实被删改得最多的一部书,却是最没有问题的《像曹操一样活着》。编辑从最保守的底线出发,凡是她觉得有一点过分的地方,都毫不犹豫去掉,完全不顾作者的心血和尊重,只顾出版的安全。等我再看到书的时候,愤怒一阵阵从心底冒出来,被删的部分恰恰都是自己觉得的语言的精华、思想的尖端,因此无异于割肉,割最敏感的肉。除了在心里把编辑的祖宗都问候一遍,别无他法。其实后来每次跟编辑打交道,我都是先跟编辑打招呼不可随意删改——这是教训之一。
最近出版的小说,内容上亦有诸多漏洞,比如错别字,比如后记忘了给我放上去,等等,总体上觉得编辑欠缺专业。
但在凤凰联动出版的《儿女培养手册》,是让我觉得超满意的一本。不论是编辑对内容的编排,还是封面设计,都大大提升文本的价值。编辑的成果令我惊喜。
相对而言,几本书在我国台湾的出版,编辑工作上特别专业,井井有条。印象最深的是,编辑把所有台湾读者不太能理解的词儿,都一一过问,该注释的注释,相当对读者负责。封面设计则超好,感觉不到瑕疵。
●编客声音
@西山书客谭旭东:策划很重要。很多编辑只会案头功夫,而且有些出版社领导也缺乏编辑思想和对文化的定位——因此出版产业乱象丛生也是这个结果呀。
@段洁:这期(《中国编客》第2期)报纸我安排编辑部所有编辑都读了,大家受益很大。
@李清扬:自从读了创刊号就期待第2期。没想到,第2期的诞生还有这么多的“典故”——感动。《中国编客》是编辑的舞台,商报编辑一定要让它繁荣昌盛啊!
@潜水荷:头版写出了营销编辑的心声,支持《中国编客》一直办下去。
@精神漂泊者:俞晓群的文章标题是第一个吸引我的,读了果然不错。先生的勤奋值得学习!
《中国编客》,欢迎您的参与
《中国编客》将秉承《中国图书商报》一贯的办报理念,以独特的视角选择自己的报道方向、以国际视野观察并记录中国编辑的生存和发展。聚焦书刊编辑群体,为广大书刊编辑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如果你有相关新闻线索,或与书刊编辑工作相关的想法、建议和意见,甚至是大的设想,我们都欢迎你发言、提问、讨论;欢迎你来稿,字数在800 字左右。如果你是书刊编辑,欢迎你的参与,欢迎你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告诉我们。
来电请拨:010-88817690(91~97)-2322
来信请发:qiwen201010@163.com
互动请加QQ:232479970
《中国编客》QQ 交流群号:140678187
《中国编客》,欢迎你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