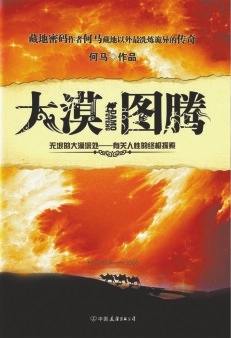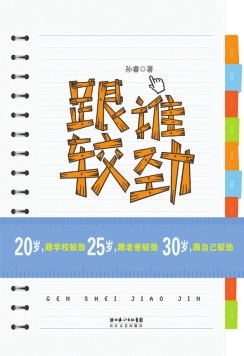《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笔锋率直,通过70多位亲历者和见证者的采访,讲述经济学人在1980年代的故事,讲述他们的理想、探索、突破,和大手笔的建功立业,首次将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群像呈现眼前,可以说,这是一部研究1980年代的碑石之作。
柳红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前助手,也是天才少年子尤的母亲,她现在的身份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过着清简纯粹的日子。子尤走后,她开始素食,做瑜伽,不用空调和冰箱,随身带着水瓶。身体的轻盈和畅快,使她的内心也变得通透起来。两年前,她开始长跑,10月24日,她参加了北京马拉松赛,用时2小时41分钟跑完半程21公里多。她作为志愿者去医院参加康复科的工作,她在北大和阿忆对谈1980年代,她用毛笔为想买签名本的网友签名,她徒步20公里去看埋于凤凰山的儿子,并将新书献给他。
柳红看起来是如此充满生机,她的研究工作也带着十足劲头,新书30万字投入了两年的心血,尽可能采用第一手资料,前后采访了70位改革亲历者。面访、电话、邮件,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和考证,以及浩大的文献阅读,支撑起这部书的厚重扎实。而文章在编辑成书时,也颇费一番思量。
柳红最近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她在2010年春,与财经畅销书作家吴晓波在媒体上就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及写作问题进行笔战。笔战后不久,3月上旬,柳红向吴晓波发出律师函,认为其所著《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出版)涉嫌抄袭她2002年出版的《吴敬琏评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部分内容。两个月后,将吴晓波告上法庭。
这是柳红第一次打官司。官司原本应该在6月份开庭,因为吴晓波提出管辖权异议,经过法院驳回又上诉又驳回的经过,拖延一段时间后,就该在北京开庭了。在柳红看来,“面对和处理这件事,对我有启蒙的意义。我们对知识产权常常不在意,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你有知识产权你就要保护好它,其实我们保护好自己也是在保护别人。”
吴晓波就此回应:因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很多情节类似。吴晓波认为,二十年来,他是一个严肃的、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财经作家,是一个以“持中正之心写作、务求字字有出处”来要求自己的人。对于创作诚意的怀疑,他不能接受。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柳红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0月版/48.00元
一问柳红 为什么要重温1980年代经济学人?
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
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中国1980年代全面启动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涉及城市和乡村。其中的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中心,最具有冲击力、张力和渗透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经过30多年,今天到了需要认真记载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时候了,更确切地说,我想把第一个10年的历史刻度划在1979年至1989年。究竟应该站在哪里看待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从经济学家群体的思想探索出发,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1980年代的时代风貌,试图为人们了解、理解、认知和研究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或者叫一条路径。
翻阅有关1980年代经济改革历史的文字记载,我们发现它们基本按照3种“范式”来组织:一是“革命史范式”,将改革历史划等于政治史,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叙述对象,研究视角是执政党和领导人,如中国改革和邓小平的关系;二是“现代化范式”,经济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改革的历史主要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制度和结构变化的历史,如企业或农村改革历史;三是“社会和文化范式”,以社会演变、文化思潮和相关人物为叙述对象,折射出经济改革,如,1980年代“文化热”的研究,隐含了对改革历史深层结构的探讨。
我想要打破这些惯常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试图让那些被遮蔽、遗忘、误解了的人和事在笔下复活。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
我无意阐述改革中重大的理论学术问题及其争论,而是通过第一手资料,采访记录,来体现这些经济学人的理想、理念、胸怀、勇气和人性。对于如今的人们,那些精神似乎久远了。因其久远,更愿意重新提起。
二问柳红
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像是什么?
三代经济学家多数已经退隐,还有一些早已不为人知。然而,他们曾经是一个群体,一同创造历史。
1980年代,有一个特殊群体,它的主要人物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将其划为上下三代。
第一代,是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既是共产党员,又充满了仁慈博爱之心。他们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先驱。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时机到来时,全身心投入,披荆斩棘,呕心沥血。
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如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
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有创见,有合作精神,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相继脱颖而出;从贡献而言,他们承上启下,将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除了以年龄划分,这三代经济学家也可以依据当时的思想资源,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等,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中国,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民国时期的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笙带出来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靠自学的人,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前受过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统学习《资本论》,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1980年代重新补修现代经济学,像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他们为让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
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视两个效应:其一,“杂交”效应。不同的思想资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导致中国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中国式的思路和模式。其二,“三代同堂”效应。任何时代都会是三代到四代的共存,但是,1980年代的三代经济学家,实在差别太大,却集合在一起。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和进展,就有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第一代和第三代,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的贡献。
■追踪报道
何马推出动物小说《大漠图腾》
商报讯 《藏地密码》作者何马近期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动物小说《大漠图腾》。《大漠图腾》虽出版晚于《藏地密码》,却是何马在创作《藏地密码》前的作品。如果说《藏地密码》是现代文明对于失落的古文明的一次探溯,那么,《大漠图腾》则讲述了一个孩子与一头骆驼在沙漠里的相处、相依、最终相互分离的故事。
何马凭借“藏地密码”系列成为畅销书作家,但本人却相当低调,并未在媒体前露面。《大漠图腾》一书的策划人告诉记者,何马是位博览群书、性格相对内向,时而悲天悯人,时而又满脑子充满奇思妙想的很有趣的人——何马不喜欢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故作深沉或刻意要保持某种神秘性,而是因为他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面对世界和自己。(风)
孙睿:《跟谁较劲》是跟自己较劲
商报讯 曾以《草样年华》走红的青年作家孙睿,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其新小说《跟谁较劲》。孙睿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系研究生时的导师、导演田壮壮为近日召开的他的新书发布会助阵,并说:“人如果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踏踏实实做到60岁,一定能做得无比优秀。孙睿目前可以把写作当成主业,拍电影当成副业。”
2004年,一本《草样年华》曾让孙睿跻身与郭敬明、韩寒齐名的青春偶像作家行列。如果说读韩寒是读他的观点,读郭敬明是读他的浪漫文风,读孙睿,则是一种幽默的现实主义风采和他对生活的解读。但和孙睿之前的作品相比,他在新作《跟谁较劲》中,认清了自己,认识了生活。可以说,“孙睿以他6年来创作的所有作品集成了一部完整的青春编年体。”
目前由孙睿担任编剧、改编其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我是你儿子》正在拍摄之中。对自己的电影之路,孙睿说:“拍电影和出书不一样,条件允许的话,该拍什么拍什么,要拍的内容,除了故事好看,还得给观众留下点什么,可能会有商业的元素,现在电影市场也很复杂,但我希望观众看了我的东西,走出电影院还有点感触,不是一乐就完事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