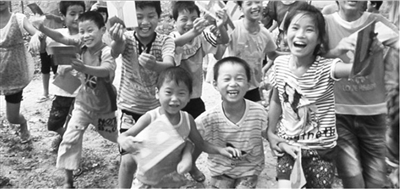广阔的中国乡村给了中国乡村教育实践者和阅读推广人以大展拳脚之空间,从书本扶贫到不断促进阅读教育革新和乡村公共生活的构建,这成为最近几年民间组织阅读推广的重大进步。但在热情之外,他们也面临着种种困惑。
背景
政府与民间达成推广共识
当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成为我国的重要国策之际,推动全民阅读,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如何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也成为全社会共同探讨的话题。无论是以政府为主导或是民间组织为推动的阅读推广,近年来都在蓬勃发展。
在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引领示范下,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在大面积建设,如投入50多个亿的农家书屋,目前已经建有38万多个,基本覆盖了中国的半数行政村,未来还希望达到全国“村村有书屋”的目标;如财政部、教育部从2010年起至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向地方拨款,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等等。此外,政府还积极组织荐书活动,如在2011和2012年度,由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组织多家媒体,向社会推荐“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试图将阅读推广活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掀起全民阅读的风潮。
在大手笔的政府阅读推动之外,另一边则是民间组织不遗余力的努力。当前的民间阅读推广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出版界所做的阅读推广,如发起儿童分级阅读的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以及儿童阅读推广人梅子涵、王林等人;第二种是以图书馆界为主力,自200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联合倡议发起全民阅读活动以来,中国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另外民间公益图书馆则成为中国儿童尤其是乡村儿童阅读的重要推手;第三种主要是学校等教育机构为主的教育界,阅读教育是教育界的核心问题,很多人都在为此探索,像亲子阅读推广组织三叶草创始人之一、深圳南山实验学校教师周其星和为全国教师、家长演讲超过百场的合肥六十二中小学部教师薛瑞萍就是其中的活跃者。
从国家战略的提出到民间的响应与推动,可以说,当下的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全社会认可的理念与行动,也成为中国社会走向阅读社会的重要路径。
民间部分阅读推广机构
立人乡村图书馆:作为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成立于2007年9月,总部位于北京。立人不仅立足于乡镇,还是沟通城市与乡村的公共图书馆网络。
梦想书屋:由腾讯公益基金会、心平基金会、经济观察报、真爱梦想基金会四方注资100万元,于2010年9月正式启动,目前已建成近200间梦想中心,覆盖近20万学生,万名老师。
天下溪公益图书平台: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成立于2003年,发起人是郝冰和梁晓燕,乡村图书馆项目的发起在2003年底,倡导把最适合、最优秀的图书,送到最僻远的乡村。
滋根爱的书库: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成立于1996年,宗旨是支持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的发展。目前,滋根已经在云南、贵州等10余个省市20个县的200多所学校和村寨设有项目点。目前已经在4省9县建立20个书库,拥有2500多箱书籍,为2000多个班级提供服务。
班班有个图书角:担当者行动是由创始人张同庆和他的五位朋友于2004年12月发起的一个民间公益志愿活动。该项目由担当者行动团队在2009年下半年启动,已在福建、江西、四川等12个省份为3.5万名贫困地区的孩子送去了6万多册课外图书。
亲近母语儿童阅读研究中心:成立于2003年7月,创始人为徐冬梅,是以“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为理念,致力于母语教育改革、儿童阅读推广和母语文化传播的科研机构。(夜 雨/整理)
探索
中国乡村提供了广阔天地
国民阅读推广要从娃娃抓起,建设书香校园,尤其是推动贫困地区的乡村儿童阅读,这已经成为众人共识,民间教育推广和乡村阅读促进已成为当下阅读实践的主要领域。
四时行,百物生,中国民间图书馆自萌发起,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生长的自由姿态。目前全国约有五六百家公益私人图书馆,它们立足于当地社区,承担着社区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的工作,众多譬如“立人乡村图书馆”、“梦想行动国际”、“担当者行动”等社会组织开展的公益图书捐助和阅读推广等项目,已经成为图书馆事业中重要的民间力量。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王子舟近年来一直关注和参与民间图书馆的发展。自2007年以来,他除了为中小学乡村图书馆管理员做培训外,还积极组织多次民间图书馆论坛,讨论乡村阅读推广。他经常看到很多民间图书馆是创办人卖破烂买书来维持的,在感动之余,他坚定认为是民间图书馆让图书馆变得更有活力。
很多从事乡村教育实践的阅读推广人是在见到中国乡村学校图书匮乏、儿童无课外书可读的阅读困境后,开始想尽各种办法为这些地区捐赠图书和报刊。但这种定向募捐并不等于能保证阅读,也很难负担图书的后续支持。在一腔热情之外,他们需要做更多的事,保证这一图书馆的后续发展,而不是自生自灭。
事实上,如果说书本是中国农村阅读短缺的硬件,从专注硬件建设转向硬件与软件兼顾的策略,从书本扶贫到不断促进阅读教育革新和乡村公共生活的构建,这成为最近几年民间组织阅读推广的重大进步。
譬如心平基金会,自2008年9月创立到2011年4季度,与数十家公益伙伴开展合作,在25个省市捐助各类学校及图书室625间。心平基金会的创始人段永平、刘昕夫妇称,他们最早想建立乡村图书馆,后来发现乡村图书室更有价值,再后来发现阅读推广才是更重要的事。作为步步高董事长,同时也是农村出身的企业家段永平,朴素地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又如作为民间公益机构阅读推广代表的立人图书馆,目前已在全国建立15所以县域为服务范围的公益图书馆,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希望藉此拓宽本地文化视野,更新本地精神生活。同时,做公益图书中盘的天下溪,在图书捐赠之外,从2011年开始,举办定期家长读书会,并举办深耕阅读种子老师交流会,联合培训一线乡村教师,以激发教师的阅读积极性。还有诸如以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以徐冬梅创建的“亲近母语”为代表的对儿童阅读和母语教育的探索和研究,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项目”等等,都在做着从提供读本资源到自行建立立体化、专业化的系统阅读教育体系的努力,做着更深层次的阅读推广。
对于当前众人对乡村图书馆各种模式的实践,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张守礼认为,以图书馆为载体,促进阅读教育创新,才能大面积和有效地促进中国儿童的阅读发展。乡村图书馆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三个中心,即作为教育基地的学习中心、作为精神家园的文化中心和作为社区平台的公共中心,除了要提供阅读,还要促进教学革新,参与构建校园文化,参与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乡村图书馆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和保证其良好运行。
困惑
阅读促进需要更多专业力量的参与
有人用美国诗人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诗句——带上水桶和抹布,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来形容这些活跃在中国乡村的阅读推广人的工作。在别人眼中,他们低调而富有干劲,他们犹如暗夜中的灯光,照亮乡村孩子的阅读之旅,激发他们对于阅读世界探索的兴趣。
阅读推广并非光靠热情就足以成事。“当下的阅读推广者要有力量,就要足够专业;如果不够专业,就不会有力量。”立人图书馆总干事李英强这样强调阅读推广者的专业性。
之所以如是强调,是因为他们正遇到一些困惑。立人乡村图书馆项目这几年发展很快,但与快速发展相比,他们更希望慢慢来,因为人多馆多,就容易面临一系列管理等问题,一方面需要专业人才的加盟,另一方面却是微薄的工资难留人。而且公益机构与商业机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商业机构可以用盈利来量化,但公益机构做大之后,常常面临追求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和困惑。
就他们的实践来说,李英强认为当下的民间阅读推广有3大问题需要解决:观念问题、人和钱的问题。“第一是观念问题,当下的应试教育造成教育界对阅读不重视,而且人们往往误读了阅读,阅读不是通往成功学的必由之路,阅读是要每个人学会独立思考,我们需要对此重新定义。第二是人的问题,即阅读推广者专业性不够,往往停留在呼吁阅读重要的初级阶段而无法拓展。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是相辅相成的,企业讲求商业模式,公益推广者也需要有影响度及推广效果的阅读推广模式,以吸引捐助人的眼光;如果阅读推广者不够专业,就无法有好的做法来吸引慈善资金的注入。”李英强说。
在李英强看来,相比国内阅读推广人的做法,国外则更为专业,他们有一系列理论研究来支持相应的阅读推广活动,比如有专业机构通过故事治疗激发阅读兴趣、纠正阅读障碍,还可以针对不同年龄人群展开分级阅读等等。
另外,在当前学校教育体系仍然是阅读推广最主要的载体和渠道下,李英强认为,有些阅读推广机构所做的很多诉诸于激发老师的兴趣,通过老师来推动阅读的活动,只能是当前教育环境下的改良之举。只有当阅读成为青少年教育中的中心环节,才能真正激发青少年对阅读尤其是人文阅读的兴趣,促进其成长。
心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松则更为乐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阅读推广是一个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期的坚持,目前已经在不断进步了。”他认为,当前乡村阅读推广的因地制宜策略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如阅读推广已经从游击战转入阵地战,从广泛撒点到实现县域覆盖或乡镇覆盖;同时在本地化上,立人图书馆就是充分调动本地力量的成功范例。但他认为本地化最圆满的结果,是通过与当地教育系统的积极参与、主动探索、不断发展,并最终改变了当地教育部门财政拨款方向,使得更多的财政款用于学校图书室及阅读。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公益和阅读推广,是全民参与,而不是做大包大揽的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