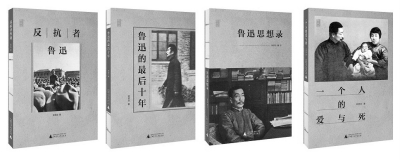鲁迅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也即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一个极其奇异的历史时期。世界上很难找到像鲁迅这样对东西方文化都十分熟悉的作家,襟怀博大,视野开阔,目光犀利;更难找到像他这样以异质性的文化观念,猛烈地抨击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革新家,一个与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誓不两立、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士。在文人社会中,他孤身奋战,那么勇敢而傲岸。同时,鲁迅又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他可以放弃学者教授的头衔,放弃世俗社会所珍视的一切,但是决不放弃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就像他笔下的那个复仇的黑色人那样,他唯以儿子般的忠诚和侠士般慷慨赴难的热忱,始终不渝地护卫着苦难的大地,广大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
在鲁迅那里,人格、思想、艺术,是一个极其健全而又充满内在矛盾张力的统一体。不但在中国,他是唯一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有的特异者。鲁迅的所有一切,可以说,都包容在《鲁迅全集》里,包容在他的全部的文字遗产中。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了解鲁迅本人以及我们自己,正如郁达夫说的,阅读《鲁迅全集》是唯一捷径。实际上,能够通读《全集》的人毕竟很有限,作为一般读者,大约只能读选本。至于读文摘本或语录本,无疑是更简捷的,而流弊,也正好出在这简捷上面。“文革”期间,以油印或铅印方式出版的鲁迅语录当不在少数,但都一律使用单一的论斗争的文字,这些文字一旦被抽离专制统治的背景,鲁迅便立刻化成了一个仇恨成性、无端挑衅、面目狰狞的“英雄”。鲁迅本人曾经打过一个调皮的比方,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所以,鲁迅是反对“摘句”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容易流于片面。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鲁迅以陶渊明为例说,世人多摘引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以完成一个“飘逸”的诗人形象,殊不知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因为他确实写过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一样的文字,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可见,倘要摘句,就得极力避免以偏概全。目下的这个摘句式选本,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编选的。编者并非那类研究鲁迅的通人,自然,该书也不敢自诩为模范的选本,但是,力求显示鲁迅思想和人格中的实质性和丰富性,确是着手的初衷。
据说,自由阅读是没有边界的。——读或不读,又或如何读,概由读者作主。正如鲁迅说的,“自己裁判,自己执行”,其实这不也很好吗? (该文为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