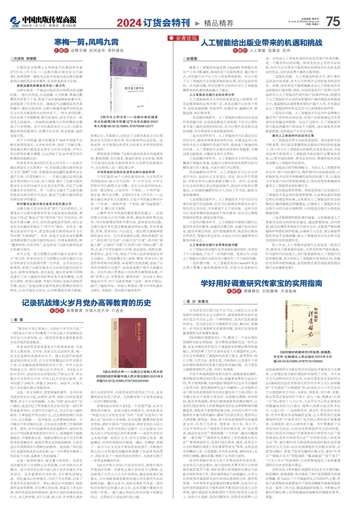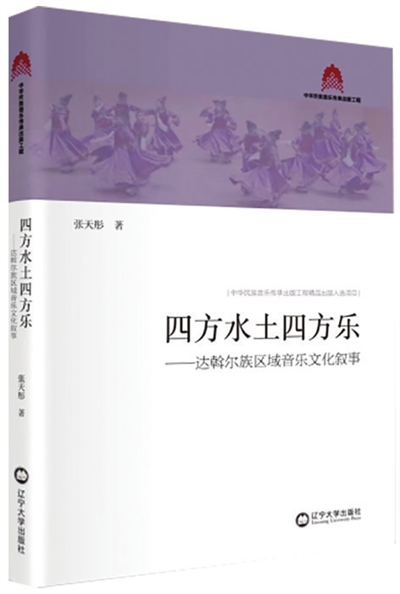○沃泽明 李珊珊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天彤教授的专著《四方水土四方乐——达斡尔族区域音乐文化叙事》,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达斡尔族整体和区域民间音乐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拯救边疆民族稀世音乐的一部力作
达斡尔族是一个被迫迁徙至东北和西北的边疆民族,一些历史传说、生活意趣、人文轶事,便通过歌舞形式传承了下来,形成了该民族独特的叙事方式,进而延续了历史和文化。随着近代边疆地区的开放和融合,族际交流加深,达斡尔族越来越多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异族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古老的民歌、民乐出现了将要断流、断代的境况,甚至于因为一些老艺人的离世,一些独特的演唱方式和珍稀曲目都成了历史绝响。在中华民族的音乐大山中,达斡尔族的传统民族音乐,仿佛空谷余音,倏忽将逝,境况岌岌可危。
似乎天有特遣,张天彤教授于2005年结缘于达斡尔族传统音乐,从开始的好奇,到结下不解之缘,将抢救达斡尔族原生态音乐文化作为使命,并列入自己研究的重点课题,从此开始了近20年艰苦的田野调查和摸排访谈。
作者及其所著的《四方水土四方乐——达斡尔族区域音乐文化叙事》一书,在抢救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遗响”方面,在拯救我国边疆民族稀世音乐遗产方面,可谓贡献巨大。一方面它通过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调查,揭示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与文化变迁的历程,开拓了达斡尔族音乐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它又提升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研究的学术层次,推动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建设。
研究整合达斡尔族古老音乐的扛鼎之作
达斡尔族古老音乐具有“碎片”文化的特点,主要是由于达斡尔族数百年来分居各地而造成的,更是由于经过“换血式”的“现代性”音乐文化冲击,传统音乐被分解、分化、同化的速度逐步加快,原生态音乐文化确实呈现出了“碎片化”倾向。尤其是一些商业旅游在开发中,更是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异化得“支离破碎”。当然,各地方言区的音乐歌舞虽然都同属于达斡尔族传统音乐,但却各具特色,即“整体相似,内部多样”,这也形成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的离合现状。
该书正是一部力图整合达斡尔族古老音乐“碎片”的力作,作者也成为了力图整合达斡尔族四方言区传统音乐文化的国内第一位学者。全书首次以全新视角,审视了达斡尔族各方言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生态,就其发展脉络、音乐流变、地区差异和不同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有条不紊的整理,从调式与调性、音调与旋律、节奏与节拍以及曲式结构等方面,指出了各地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歌舞的异同与特性,以音乐理论为指导,以田野调查实例为根据,客观公正,不落窠臼,总结出了达斡尔族各方言区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沿革、相互脉络和社会价值。这些成果,无不体现出作者扎实的音乐学养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特别是该书明晰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的地理布局、整体面貌、音乐谱系、体裁归类和文化价值,体现了目前国内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完全称得上是一部扛鼎之作。
中华民族的交响乐应该有达斡尔族的和声
中华民族是56个兄弟民族用血肉、文化和历史共同组成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都不会完整。音乐文化也同样如此,如同一部交响乐,少去任何一个和弦、一个和声或一部乐章,都不会完整。这部《四方水土四方乐——达斡尔族区域音乐文化叙事》,正是中华民族交响乐中的一个乐章、一部和声或一个和弦,她“高起低落”,乡音旷古,稀少而又难得。
山歌作为中华民族民歌的基本体裁之一,泛指田野乡村的人们在行路、砍柴、耕耘和放牧等活动中,为抒发感情而唱的节奏自由、旋律悠长的民歌。达斡尔族许多扎恩达勒就属这样的山歌,其中有爱情、苦难、更有向往,可以说是一部达斡尔族精神家园的音乐史诗。它与各民族的山歌,例如青海的“花儿”,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长调”,贵州的“侗族大歌”,江浙的“吴歌”以及四川的“西岭山歌”,等等,汇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合唱,此起彼伏,南腔北调,相互呼应,各有千秋,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和人间烟火。然而收集它们,保留、整理、传承它们,却是件异常艰辛的事情,毕竟现代化的浪潮,卷走了太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每想起都不禁令人扼腕长叹。好在作者以其勇担大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终于为读者奉献了这样一部学术精品,践行了她始终如一的初心和使命:要为中华民族的交响乐,保留住一段达斡尔族的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