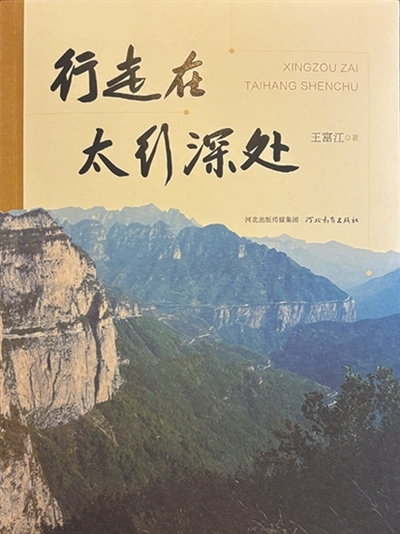○苏有郎
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人们往往以一些名山名水作为某种象征,太行山即是其中之一。关于太行山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太行山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太过丰富。探寻中华文明之源,太行山是无法绕过的一个存在。描写太行山历史文化的文学作品不少,但像王富江《行走在太行深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这本散文集,却不多见。
王富江从小生长在太行山区,注定他不像一般人作为旁观者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采风式,体验三五天,或者六七天,回家再翻查资料,抒情风景,咏叹历史。他的根在太行深处,他的情在太行深处,太行山的山风山石山泉山树滋育了他,言行带有“王家儿女基因汩汩流淌着崇武尚勇的遗风,蕴藏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气神”。他以太行之子的身份,全身心投入,既有旁观者的冷静,又有亲历者的深情,年轻时从太行深处走出,在外工作多年,又回过头走进太行深处,仔细抚摸品味,进一步深入历史,进行文学描述,哲理思考,与一直生活在太行山的乡亲不同,与非太行山生长的“外人”也不同。他的感受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距离说”“移情说”。
书写中华文明和精神的手段千千万,全面的、大而全的宏大叙事固然不错,但抓住一点,旁及其余,岂非高明之举!王富江没有面面俱到,他选取了与家乡太行山有关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和事物,揭示太行山的历史文化内涵,深挖太行山作为“中国之脊”的精神内涵。他数年奔走,书海遨游,遍寻燕赵慷慨悲歌的源头,无数次出入这道威武不屈的民族脊梁,留下一串串鲜红的印迹。他漫步华夏民族生存空间与地理概念中的“天下之脊”,不经意间打造了一道太行厚重文化的风景线。
作者写家乡的赵孤庄,得出结论:“一滴水,映射太阳的光辉;一大义,凛然千秋照汗青”“勇于担当我将无我的浩浩亮节,澎湃在中华儿女的心里,也共鸣于四方人的胸怀”“纵观当今五洲四海,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广泛认同。”(《赵氏孤儿溯源》)
从对家乡天梯山的历史思索中,感悟到:“洞藏冀南民间抗金历史稀少的几束光芒,让我们有机会面对宝贵的文物,了解当年的危机四伏,面壁思考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天梯山之光》)
作者有感于太行东麓人文荟萃,承载了中国山水文化由宫廷走向民间的发祥地,“日复一日,走深走实一幅幅交相辉映的山水立体画卷,入脑入怀人类历史进步的层层文明碎片;年复一年,追风逐月明暗流动的古今网红打卡地,只为把血脉相连的根用心留住。”(《太行东麓十六峰》)
作者有感于巍然而立的太行“天下脊”对华夏文明形成的举足轻重。走进绿色太行红色太行厚重太行的深处,放松心情,放飞自我,一步步感知和品味“中国之脊”的伟大风采和雄浑内涵。
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王富江是一位忠实的践行者。故而,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硕果,其感受是独特的,其发现是独到的。但他并不满足于自己作为太行山人先天的那种狭隘的“小我”之情,而是站在大历史的宏观角度,进行理性思考。为了深入研究“河套王”王同春,他曾专门去河套采风;为写太行八陉,曾数次往返调查;为写云梦山和鬼谷子,他走遍了全国所有与鬼谷子有关的云梦山……
正像贾兴安先生为此书作的序中所说:“用准确而富于色彩的文学语言去表达,让那些呆板的知识和教科书式的资料,都变成动态的可感知的,饱含情感和温度。”因此,王富江写鬼谷子与云梦山,写豫让,写紫金山五杰,写八路军司令范子侠,写父母,写《家在王硇》……乡情乡韵里面,饱含着家国情怀;历史名人的追忆,影射着自身的追求。每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家国情怀的一次深情抒写;每一句文字,无不关注国家命运。
有人把《行走在太行深处》归入大文化散文范畴。大文化散文,自余秋雨掀起高潮以来,一直延绵起伏,皆因这种文体不仅容量大,其主题具有极强的张力。它突破了一般传统散文的格局,使人耳目一新。近几年,人们对大文化散文已不再热议,但不热议并不代表不关注,它一直在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着,已成为一种成熟文体。《行走在太行深处》便是新开的一朵鲜花。作者不去与别人争高低,没有步人后尘亦步亦趋。作为写诗出身的作家,王富江的语言特色非常具有辨识度,他充分运用诗化的语言抒情,悠远而味长。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读者和作者,都不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旁观者,绝对的旁观者是没有的。人们总想从中发现与自己关联的故事和主题,所谓“带入感”和“代入感”。作者投入,读者被“带入”或“代入”。
作为文学作品,我们如何探寻与书写名山名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如何书写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以,作者神交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代英雄,遥思落地生根的千古卓识,追念中华第一骑兵团的卓越风采,得出“永不磨灭的,是他根植在华夏大地的胡服骑射精神”结论。他在《豫让悲歌》中叹道:“豫让,赵襄子,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却上演了一出‘忠孝仁义勇’绝版大戏,为三晋和燕赵大地,注入了永远无法磨灭而又发人深省的文化基因,不仅夯实了区域文脉的根基,而且盘结成中华文脉重要的根系。”
太行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一,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太行文化血脉,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它滋生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从太行写到了河套;从《黄巢峡里的黄菊花》写到《汉水润邢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古至今,辐射中外。《鬼谷子和云梦山》《西山觅王禅》写的是中国哲学智慧,《神医扁鹊》写的是中国医学精华,《赵氏孤儿溯源》《豫让悲歌》写的是太行豪气及义薄云天的燕赵慷慨悲歌之气,《仰望赵武灵王》《在韩信岭上》写的是决定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英雄情怀,《吟诗太行第一人》《李攀龙的诗》说的是太行文化的滋生与深厚,《河套王》写的是一介贫苦百姓是如何艰苦创业担起国家大任;《太行八大陉》验证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著名论断:“太行为天下之脊梁,谁控制了太行,谁就可以得天下”。而《范子侠将军》《故乡的英雄们》《沙河血脉感怀》更是直接对太行精神血脉进行了思考……
作为一部散文集,《行走在太行深处》中各篇并无联系,但放在一起,成为一本书,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存在,集成了太行山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体系,充满了统一的精气神,竖起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历史文化格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视域宏阔,气势辽远,主旨深刻,意味悠长。
恩格斯说:“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作者写父亲的厚道、母亲的慈爱,写乡邻的淳朴,写故乡的风俗民情,无不折射着中国文化的基因。
我们应该如何写家乡的山水人文?如何深挖名山名水所包涵的精神本质,寻找中国的精神血脉?王富江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极少在行文中发表长篇大论,也很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不动声色地融入叙述之中。他在多篇作品里强调,太行山是“中国之脊”,其用意不言而喻。他的思考很多地方是独特的,这正是《行走在太行深处》的独特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