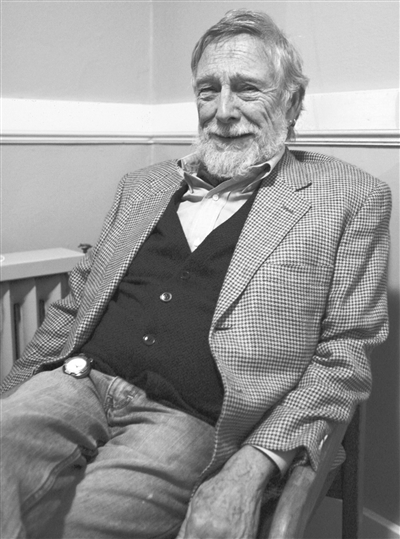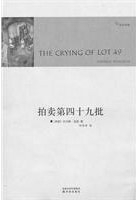品钦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且不谈喜欢品钦的,喜欢美国文学的,夸张一点说,只要稍稍与文学阅读沾一点边儿的大约都知道他的《V.》和《万有引力之虹》之类的。这部《拍卖第四十九批》还未全本译介到大陆的时候,不少人已从美国文学研究界知道了它的大概。但等拿到手后,我还是有些吃惊。无论是与专家们的推崇相比,还是与早已读到的品钦的其他作品相较,这部长篇总让人觉得太“轻”太“薄”。虽然美国人并不是总喜欢砖头般的大部头,毋宁说十几万字的长度更让他们情有独钟,海明威、塞林格、贝娄等等,这样的长度在他们手里都曾玩得炉火纯青,臻于化境,使人忘却了“篇幅”的概念和存在。但以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品钦与他们不同,他是一个喜欢“复杂”叙事的作家,多线索,多人物,含混,缠绕,一直是品钦的标志性风格。《拍卖第四十九批》之前的《V.》,之后的《万有引力之虹》等作品,虽称不上卷页浩繁,但篇幅也都是《拍卖第四十九批》的几倍,据说《万有引力之虹》之后的作品大都堪称巨制。
然而,篇幅只是一个外在的存在,有时,它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就一定简单,对它的阅读就一定容易。译林社的这本叶华年的译作不过12万字,但这十多万字足以给读者设置无以计数的阅读障碍。品钦依然运用的他的拿手好戏,他会在作品的一开始就使读者预感到故事的复杂,他总是那么自信、从容,他会让他的暗示一一落实和兑现。奥迪帕·马斯太太“被指定为一个名叫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的加里福尼亚州房地产巨头的遗嘱执行人,或如她所认为的是遗嘱女执行人,而那巨头在他业余消遣中曾亏损了200万美元,但依旧拥有数量众多的缠结不清的资产足以使它的全部清理工作不只是一件名誉性的事情。”这个开关所包含的信息已足够多了,有经验的读者已经由此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奥迪帕是谁?皮尔斯又是谁?他为什么要奥迪帕做他的遗嘱执行人?遗嘱又是什么?皮尔斯如何“业余消遣”?又是怎么在此中亏损的?奥迪帕将如何开展工作?不管怎么说,品钦已经清楚地告诫我们,奥迪帕面对的是“缠结不清的资产”,这注定不是一桩走过场的程序性质的“名誉性的事情”。其实,这还只是该书一条表面的叙事主线,随着奥迪帕工作的展开,众多的人物,奇异的场景,神秘的事件将纷至沓来,而那些永远不可能解开的一个个谜团犹如巨大的黑洞又将出现的一切吞噬殆尽——品钦表明,作品的复杂程度并不与篇幅成正比。
品钦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复叙,要将马乔、奥迪帕、皮尔斯、梅茨格、麦克、曼尼、内法斯蒂斯、科恩等人物以及围绕他们的故事说清楚是桩非常困难的事。我感到兴味盎然的有两点,一是以奥迪帕为线索的对神秘的探寻,它使《拍卖第四十九批》类似于一部侦探悬疑小说,毫无疑问,它融入了我们称之为通俗文学的许多元素;第二个就是品钦对许多科学现象、原理的文学化叙说。本来,科学与文学是不相融的,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科学开始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并且越来越成为人们解释世界的方法,但是将科学作为文学的叙事对象,或者以科学的原理与观念作为文学作品的内在语义在文学中并不多见。学术界对品钦的创作阐释得相当充分,我以为这两个方面足已使后现代主义在品钦身上绝非标签。
对于任何一部作品来说,它的意义与价值在相当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接受的语境,翻译作品尤其如此。且不说林纾的翻译,也不必上溯到“五四”,即以中国新时期文学而言,域外作品始终是中国文学的镜子,甚至是源泉和榜样。如果以品钦作为一个视点去思考中国文学的一些变迁会使人越发感到品钦的强大和执着。也许,品钦的创作历程对于他自己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来说,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涌出的那一批先锋作家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已经无法企及的高度,套用一个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句式来表达,那就是一个人先锋一阵子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先锋而不妥协。而品钦几乎就是一辈子的先锋!《拍卖第四十九批》是品钦的第2部长篇,前有《V.》,后有《万有引力之虹》,再有《葡萄园》、《梅森和狄克森》、《逆时而动》、《内在的邪恶》,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让人对其后现代的玄奥惊叹不已。《内在的邪恶》出版消息公布时,品钦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不仅是他的作品,更有他的性格与处世方式都使他站在两个世纪的先锋之巅。
品钦是独特的但不是孤立的,他呼吸的是美国是世界的气息。品钦的先锋是从里到外、彻头彻尾,既是形式的,又是精神的。品钦的小说形式确实令人着迷,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内在精神气质,这也许是他能一辈子先锋到底的根本,而这恰恰是中国先锋文学所缺少的。想当年,中国的年轻人在小说形式上玩得也不差,而且也不能说形式就不需要,1990年代初韩少功就说过这样的话:“可以玩一玩技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在汽车、饮料、小说行业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技术引进的初级阶段往往有点混乱,比方用制作燕尾服的技术来生产蜡染布,用黑色幽默的小说技术来颂扬农村责任制。但这都没有什么要紧,除开那些永远不懂得形式即内容的艺术盲,除开那些感悟力远不及某位村妇或某个孩童的文匠,技术引进的过程总是能使多数作者和读者受益。”但这位作家好像早就有先见之明地说道:“问题在于技术不是小说,新观念不是小说。小说远比汽车或饮料要复杂得多,小说不是靠读几本洋书或游走几个外国就能技术更新产值增生的。”先锋文学为什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日趋式微?在形式,更在背后丰富的精神存在。所以推究起原因,可以说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从内部讲,当时先锋文学的兴起存在着许多准备上的仓促和条件上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先锋文学先天的不足,后天也就更难调理了。这准备不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观念、人格、价值与世界观诸方面的因素。因为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把先锋文学更多地看成是一种形式上的断裂与反叛,这也就是后来动不动在理论与实践上将先锋与实验混为一谈合而为一的原因。其实,先锋更重要的品格与特征显然是思想上的,是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这些元素如何以文学的语言方式呈现。如果还要为中国的先锋文学招魂,一方面一定要走出先锋等同于实验形式的误区,以防止过度的甚至是恶劣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就是要关注先锋文学的现实生活基础,因为先锋文学的精神之花总是离不开当下社会现实的催生,也只有接通了两者,先锋文学才能成为现实精神锋线的代言;再一方面就是作为先锋文学的创作主体必须摆脱对他者的依赖,倡导并践行本土的原创精神,只有从根本上克服了哲学的贫困,中国的先锋文学才能拥有永远进步的姿态与实绩。
我不认为这个话题已经过时,因为在当代及至今后,先锋永远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甚至是文化的活力的体现。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我们懈怠的时候就想一想品钦吧。
《拍卖第四十九批》[美]托马斯·品钦著 叶华年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