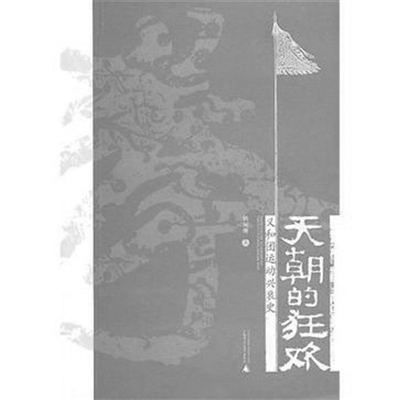不能否认,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对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对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和对抗意义,被视为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反映。但,疯狂的反抗、报复导致的非理性杀戮,不仅使两百余名传教士、两万多名中国教徒死于非命,且有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遭到了致命的戕害。
在特殊意识形态下,不少人对义和团运动赋予了正义、肯定和激赏的评价。然有史家学者却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迷信、暴力、荒诞、混乱、恐怖、反动和顽固。李大钊在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唐德刚一针见血地将义和团批判为一次清廷的权力纷争。这些,我们在鹤阑珊《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兴衰史》,不难找到相应的内容。
义和团的兴起和壮大,并不具有统一的领导者、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纪律性,如同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花拳绣腿,祭神念咒,烧香祷告,装腔作势……这些荒唐的把戏,麻木了被现实逼往绝境的百姓、流民、小手工业者。他们在艰难时世惨淡度日,痛苦挣扎,寻找生存的隙缝与喘息的瞬间。船家女儿林黑儿自称“黄莲圣母”,组成红灯照,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执红折扇,红满半边天。流浪船夫张德成一次从官府救出几个练拳的年轻人,便成立坛口,自称“天下第一团”,聚集了上万之众……一些酒肉和尚、地痞流氓,铤而走险,成为了一方坛口的大师兄。他们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被呼为“活神仙”,完全是因商埠的开放、租界的圈定、洋人对居民的压迫所致。
德国集团欲将山东划入势力范围,频仍制造事端,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多方挑衅,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京飞扬跋扈。但,中国最高集权者慈禧,断然不会容许外来势力对其权威的蔑视和挑战。此前西方列强干预她废黜光绪,使之计划破产;如今得报西人集结兵力,逼其归权于帝,更让她出奇愤怒了。她重用载漪、刚毅为代表的主战力量,颁令原本仇视的拳匪为义民,似乎无惧地向十一国宣战。
义和团的斗士们,原想过些安稳自足的日子,而机遇屡屡不得。他们从最初的反清复明,发展到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却自始自终不曾改变命运,即便踏进过暂时设为坛口的王府、衙门,但当权者在利益遭受损害时,自会无情地抛弃他们,甚至赶尽杀绝。我们在痛恨西方侵略者和慈禧之流之时,该冷静地看到拳民们的迷信、愚昧、疯狂和麻木。他们反对西洋教的迫害,也欺辱、剿杀、迫害自己的同胞,干了不少中伤人道、破坏社会的蠢事:杀戮老幼,集体屠杀,火烧民宅,挖断铁路,摧毁衙门,焚坏车站,砍倒电线杆……留给我们的,是感伤和苍凉,无奈和哀痛。
历史不会因为尘封、扭曲和篡改,及意识形态,而有所改变。鹤阑珊借助文献史料,在《天朝的狂欢》中,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解读义和团运动的兴衰成败、是是非非,尽可能地作了公正的叙述。事与景穿插而行,理同情交融一体,不同利益代表、不同价值取向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品格、心理、事功,一一重现在那一段斑斓的、屈辱的、悲烈的而并非光彩的晚清历史中。
我们要坚持平视的眼光,辩证思考,看清当时政局和国际纷争下不同人的选择和作为,认识和把握西方列强文明实质。洋人们不远千万里地来到中国,不是简单地要胡作非为,而是寻求资源、扩大市场。而从乾隆朝开始,中外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朝廷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成为触发或激化中外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礼宾常识,于当时看来,却是“体制攸关”的大事,不能让步。这背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国体。长期宗法制统治和闭关锁国造成的愚昧,影响着中外交往的正常印象。当时中国外交,动不动以赔款割地为筹码,结果是不愿吃明亏而吃了暗亏,不愿吃小亏而吃了大亏。
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列强在中国扮演侵略者的角色,在中外冲突中,中国是正义的一方,却很少发现缺乏法律意识的拳民、教民和昏聩的官僚,具有争取、忍让的开放心态。某些眼光远大者,在策略上暂时、局部和必要的妥协,也被一律斥为“卖国”。更多的利用、盲目、迷狂、悲烈和无可奈何,影响了后人不能站在历史风云时局中,正确辨识真实的历史。这一场所谓反帝爱国的运动,并不具备严格意义的革命性质,而列强迫使清廷以每一个中国人赔壹两白银的威逼,成为晚清史上最大的一次悲屈和耻辱。拳民们被逼后的激烈反抗,被当权者、主战者们不辨时势、推波助澜地利用、玩弄,成为了廉价的、不光明的御敌工具。当我重温这一场中国百姓、洋人和清廷的大博弈,不由感叹袁世凯、聂士成甚至光绪帝主张镇压义和团的长远考虑,也不由想起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的清醒与冷静,在帝制和耕读文化的余晖中,不得不被覆灭,成为不能忘记的祭品。
《天朝的狂欢》鹤阑珊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