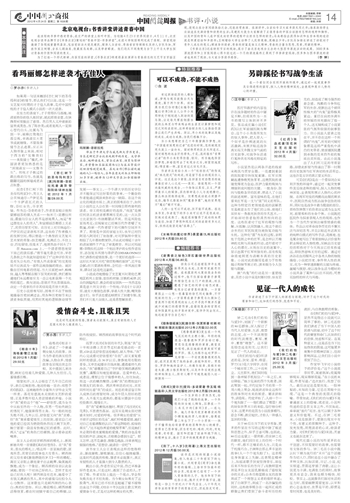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杏仁树下的圣母玛利亚》的情节,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才子佳人故事,是对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小说的一次大逆袭。
在东方的语境下,才子常得匹马落魄,被清丽绝俗的佳人拣回家,就此郎情妾意,在扶携帮衬里酿出了感情。然后男人又冲着新的富贵或美色,当了陈世美;或者是两人一见倾心誓约白头,比翼鸟飞到一半,被棒打鸳鸯打落尘埃,幸遇清官大老爷成就姻缘。不管故事情节怎么进展,反正从人物形象上来说,相对于西方的“优雅贵妇——英俊骑士”模式,中国读者更加熟悉的是“深闺淑女——文雅书生”。传统才子做过的最出格的勾当,也就是翻翻花园的围墙或者点点秋香。
而在《杏仁树下的圣母玛利亚》中,男主人公贝纳迪尔·卢伊尼是一个卡萨诺瓦式的人物,吞吐女色,尽享欢愉。作为达·芬奇的弟子,作者甚至暗示他和蒙娜丽莎的情人关系——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最能勾引女人的不是漂亮男人,而是“有过漂亮女人的男人”,和蒙娜丽莎都搭上关系了,其资历厚实可知。在历史上对贝纳迪尔·卢伊尼的记录语焉不详,这也给了作者极大的发挥空间,得以塑造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形象:技艺精湛、充满活力、不信上帝、四处留情,但是末了,他居然浪子回头了!
在 Amazon.com 上,一个读者愤怒地留下自己的读后感:“情节毫无悬念可言,早在几条街之外我就知道结局了!”这种评价其实是有失公允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不应该成为一部作品被指摘的理由。就好像在任何电影的结尾,当大反派把007、蜘蛛侠、超人等等踩在脚下狂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永远都要反戈一击让电影获得一个光明的尾巴。换句话说:悲剧并不比喜剧高尚,决定一个故事的并非其结局是否皆大欢喜。
历史小说很难写好,困难并不在于细致地描摹历史回溯过去,用各种历史细节来让读者身临其境,用其时其地的逻辑推动情节发展——事实上,一个牛津大学的历史学位并不能保证写出好看的故事来,一个勤奋的作者能通过阅读来弥补这一缺陷。在这个商业化的阅读市场上,真正的困难却在于,如何让小说的主人公在第一时间吸引那些势利的读者。帝王将相是最好的选择,“戏说”是操任何语言的读者都喜闻乐见的,这一点从莎士比亚到丹·布朗都屡试不爽。但是风险也显而易见:宫闱秘史已经被历代作者嚼了无数遍,给新一代作者留下的可操作空间并不多了。即使是中国的家庭主妇,也早已对四阿哥八阿哥们了如指掌,对刘罗锅和中堂互相掐了几年都如数家珍,并由此对绵延十余年的清宫剧终于产生了审美疲劳。所以对玛丽娜·菲欧拉托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性作者而言,添加复古风情与蒂萨诺(DISARONNO)杏仁酒香的爱情故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好比大家天天吃“御贡粉摊的面饼”,迟早也会腻;但只要洒些香料,念叨出一串风流往事来,群众们还是吃这套的。
小说成功地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伦巴第地区的风土世情,世俗的欢愉、宗教的戒律、民众的狭隘残忍、教会的虚妄固执——当然这也算是意大利文学的一个传统:早在《十日谈》里,就有大堆情色故事,举着人性大旗,嘲笑修道士们。似乎谈恋爱还顺便反了封建专制,美男们不只是大众情人,还是思想解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