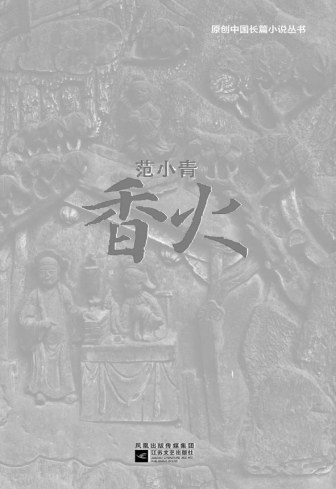《香火》是一个让我从根本上改变了阅读姿势的小说。感觉有点像坐过山车,意想不到的人物关系及它们之间似乎不对称的位置与组合,一次次,搅得我几乎有点转向,有时甚至感觉到一种被颠覆的感觉,又转回来,那车仍在轨道中。作为文化图像的香火到底怎样一脉相承地延续?而太平寺里的香火(孔大宝)仅仅是一个不通佛学的勤杂人员吗?香火的命名仅仅是一个符号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喻义?
捋一捋小说《香火》中的人物关系,香火的爹孔常灵和香火的儿子孔新瓦,加上香火,似乎是一条承续“香火”的血缘链。从小说的内容分布来看,孔新瓦的笔墨很少,小说所剪裁的时间段基本属于前孔新瓦时代。而从香火爹的角度,小说所试图展现的生活内容则属于他的后事。该书中,这一不可逾越的生死边界被打破,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在香火与当下生活的交流互动中,香火爹似乎始终在场。
由此可见,《香火》与我们习见的小说的最大不同,是它改变了常规分类,让生者与死者的坐标轴交叉、重合、甚至互动。《香火》也不同于那些穿越小说,该书中的生死边界则是始终模糊不清的。在香火那里,甚至可以说那边界始终打开,容他进出自如且不自知。这就是说,对于香火而言,生生死死,他自己似乎并不很清楚。取存在的角度,死对生,似乎不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取文化的角度,死与生,从来都是一体的,倒是对生没有影响的死,才是荒谬的。也正是从这个高度,小说才设计出这样一个无界的存在与感知,让香火(孔大宝)成为勾通过去与未来的“使者”,让昨天对今天产生影响,让死对生有意义。从而让延续至今的一脉香火穿越生死边界延续下去。
在小说结构方面,香火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一个大段落,有两个主要事件,一是到庙里砸菩萨,一是到阴阳岗去掘祖坟。砸菩萨与掘祖坟,都是那年头比较典型的“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事件,寺庙里的和尚大师傅、二师傅与村干部三官、以及老屁等底层的民众,都被卷入其中。这里并非确指某种宗教信仰,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
那么,所谓“四旧”到底是什么?它与文化传承是什么关系?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在以孔万虎为代表的造反派面前,其定义是确定的,不然大家就不会都去破它。然而,用普世价值去看,用恒久的视角去衡量,这些被强力破坏,恰恰是后来又一一修复且继续延续下去的东西,那么,为何这些东西在那种强力背景下竟然没有被彻底破掉?那恰恰是因为“孔常灵”的意义所在,“孔常灵”(香火爹),其实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根性。
从第五章开始,用倒叙的方法,阐释孔大宝为何能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可以出入生死边界而不自知。作为小说,需要读者能通过人物、场景、事件等元素,或曰通过小说手法的合理性,信服地抵达小说的虚拟真实。因此,第五章是极其重要的一章,譬如一个环扣,它设置了孔大宝作为一种异数的因由。而从这一环扣,再返观小说的前后,许多东西被贯通。
这时,再来想小说的题旨。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段,发生的一些似乎只涉及寺庙兴毁、祖坟毁建的乡村事件,它们为何能让读者心旌摇颤?!
除了香火命名的张力,还有掘祖坟的隐喻。这里也有两层含义。现实意义中的掘祖坟很好理解,而文化意义上的祖坟被掘,则需要带入更多的历史思考。掘祖坟事件,随着所谓的“破旧立新”成为往事,谁也没有真正破掉“旧”,没有。人们看到许多当年被破的东西一一复辟回来,只是有一些东西却始终回不来,这是令人遗憾的事。这是文化的悲哀,也是香火作为文化图像的隐喻。当我们从文化图像的角度来解读小说,就能明白这里面所说的寺庙、佛教,并非实指宗教,它们有更大的隐喻空间,标示着更阔大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佛教、菩萨、祖坟等等,其实仅是一种指事或会意。
从文化图像的角度阐释小说,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悖反:从卑贱者最聪明,到高贵者最愚蠢……等等。前面说过,寺庙里的香火与和尚属于不同级别,一是主业,一是打杂。而“香火”的传承偏偏是一个不通佛理的打杂的人在做,反倒是一个不通佛理似乎愚顽无知的寺庙勤杂人员,他维护着寺庙,闯到县政府找县长要修复寺庙的批文,并不惜变卖传家的玉器用以修复寺庙,真正的“香火”就是这样传承下去。宗教、文化、甚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有时恰恰是这些固执甚至愚顽的人,他们使之历经周折,坚持下来,并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