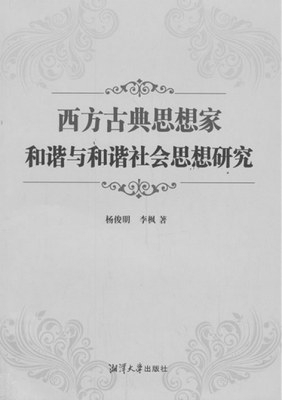杨俊明教授与李枫教授合著的《西方古典思想家和谐与和谐社会思想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上穷碧落,下搜黄泉”,对古代西方“自毕达哥拉斯以来至斯多葛学派”的众多思想家有关和谐与和谐社会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专著。此书的研究,既关注诸多学派的思想在自身扬弃过程中的变化,也关注学派之间的相互影响。此类研究视角,在国内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中是不可多见的。
当今世界各地区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胜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这种情况的形成,为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汲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于国家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自近代中国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然而也留下种种令人叹惋的悲剧。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入反思西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研究》一书不仅深入探讨了古代西方的“和谐与和谐社会思想”,而且注意到此类思想对于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因此,此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一书逻辑思路严谨,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采用考镜学术源流的方法,揭示了古典时代和谐及和谐社会思想的萌生与流变情况。以“和谐”之概念为例,书中将和谐思想的源头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毕氏用“和谐”一词来形容对音乐的体验。在古代拉丁语中,“和谐”作haimonia,亦先有音乐清晰协调之义;古汉语词汇“和谐”同样具此含义——譬如《晋书·挚虞传》“施之金石,则音韻和谐”语。中西文化中的和谐一词,盖由对音乐的形容引申至其他领域。所以,和谐根源于对音乐的体验,也就包含了对客观事物的某种主观体验与感受。而主观体验与感受和个人经历、关注角度、思维方式及心理状况有联系,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据此,作者指出:要设定一个永恒的和谐标准是很困难的。随着社会的变化,“和谐”的涵义必定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西方古典思想家对“和谐”概念存在种种不同解释的原因。其二,全书的逻辑思维层次严密。作者指出,尽管西方古典思想家对“和谐”涵义的理解,存在种种争议,然而其异中亦有同。大多数学派对“和谐”的理解,均可归为三个层次: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之自我和谐(“求诸己”)。此三个层次,由外而及内,反映出人类对自身反省的不断深入。其三,重视学术思想形成的背景。作者对各主要思想流派形成的背景(即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状况),安排专门的篇幅加以论述,从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各流派的和谐思想。
更值得提出的是,该书的研究注意到了西方古典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思辨的逻辑思维与经验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在某些西方思想家看来,“和谐”可以超越于历史而具有永恒性。如毕达哥拉斯所谓“数的和谐”。此类“和谐”之涵义,尽管没有完全摈弃历史,然而实际上并不是基于历史的思考,而是一种脱离历史的观念的思考。作者指出,西方思想家也注意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所谈论的“当时的社会”,就蕴含了对于此问题的认识。西塞罗对此问题则有相当深入的思考,西塞罗认为,“自然的正义”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体现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就是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而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就是社会和谐形成的基础。西塞罗的思想深受希腊化时期斯多噶学派思想的影响,这位杰出的罗马思想家与斯多噶学派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思想并非局限于理论思考的层面,而是深深植入于历史与现实之中,所以他提出,社会和谐最终要由建立在权力相互制约基础之上的“混合政体”来实现。西塞罗的思想,反映了重视思辨的希腊思想与重视经验的罗马思想的融合。这种把先验的“自然正义”与历史与现实之中的正义与公平相联系的思想,对基督教“两个世界”神学观念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研究》一书对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均多有新见。例如,作者对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几种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梭伦的政治思想,埃斯库洛斯的艺术思想,阿尔克迈翁的医学思想以及毕达哥拉斯的科学与哲学思想)加以探析比较,并发现了它们的共同属性:“主张对立面的中庸与和谐”。作者以此为由,将上述思想归为一种“新思潮”,进而把这一“思潮”与彼时希腊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联系起来。又如,其书在对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将“赫拉克利特的和谐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亦即“‘和谐’乃是一种冲突的、动态的……对立面的统一”,遵循“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正义”,以及“遵照‘逻各斯’的要求行事”。基于这三个方面,作者对赫拉克利特的和谐思想作出评价:“把和谐从天国拉回人间”。再如,作者通过对柏拉图有关和谐社会思想的分析,概括出柏拉图和谐社会思想的四点“历史启示”: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利益均衡与个人和谐。其中,作者在讨论“公平正义”一项时强调:“柏拉图的公平正义观对今天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颇有启迪”,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制度层面加以保证,却是当代中国人所担负的一项既极为迫切,又非常需要智慧的历史使命。品读此书时,读者会为作者笔端时常流露出的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所打动。
《研究》一书,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社会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