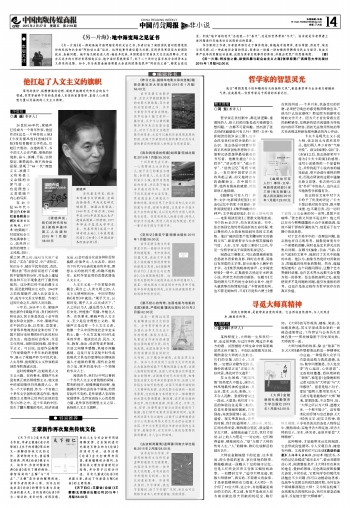他以“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彰显着哲学与生命相互碰撞的气质,完美展现一位哲学家关于阅读的私家记忆。
哲学家在我们眼中,都是讲逻辑、重理性的人,给人们的印象是成天皱着眉头想问题,一点都不可爱风趣。然而读了张志扬的《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全三册),也许会改变我们对哲学家的片面认识。张志扬是中国哲学界真正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学者,堪称汉语思想界最受敬重的书写者。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却又抱持独有的清醒独立。在中国哲学界,他具有极高的威望,然而却惊人地低调。
《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主要由《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E弦上的咏叹调——电影阅读经验》三册散文随笔组成。书中的40余万字,均为首次发表。书中,张志扬回忆他传奇而曲折的生命历程、难以释怀的人生故事和独到另类的文艺感悟。他以“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彰显着哲学与生命相互碰撞的气质。人生、文学、电影三重妙门之内,尽是一位哲学家关于阅读的私家记忆。
阅读这三册散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志扬读书思索的身影,同时在朴素、简练且有深度的文字里,显示出他令人嫉妒的才学。在《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一册中,汇集着张志扬近年来研读小说、欣赏艺术的真切感悟。在题为《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的文章中,他开头就真挚而热情地写道:“不管高更如何,也不管毛姆如何,只有《月亮和六便士》摆在我的面前:一个多月来,我备受它的折磨,必须把它唤出的感受精灵释放出来。”他为什么如此感叹?那是因为他感叹毛姆的文学天才。因为天才首先带着生活的新鲜感受,发现新的层次或属性为传统的内容所不相容,因而无法借用传统的形式来表现这种新发现所激活的内心冲动。卡夫卡是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张志扬尤为喜欢其作品,他们两人多少有些“气味相投”。读完《城堡》、《法门》、《圣旨》之后,张志扬挥笔写下题为《卡夫卡距离》的感悟。他写小说感悟的一个显著特色,并非拘泥于小说内容的铺陈叙述,更不会进行感性的赞美,而是在研读的过程中碰撞出独立思想。张志扬可以说是“书评”中的高人,也许这正和他的哲学底蕴有关。
张志扬在文章中对卡夫卡给予了优美的评论:“卡夫卡想以绝对的否定性,既不要城堡,也不要自我,而一切归于寂静,这是全善的另一世界,思想不在喧哗。”张志扬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之所以在当今熙熙攘攘的大众中优雅低调,是他不屑于那些所谓的名气,他更乐于在宁静中放逐思想。
对于艺术美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张志扬也有自己的思考。抽象是审美当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也是艺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题为《抽象:自由,气韵,自由气韵》的文章中,他探讨了艺术中抽象的本质。他认为,抽象当然是针对具象而言,即超越具体形象的限制。然而,超越有限度吗?这个问题问得好,让整个艺术界顿时语塞,也许艺术界永远都不会有整齐划一的答案。张志扬的高明之处,就是使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能引发重新的思考。这也许是张志扬作为哲学家存在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