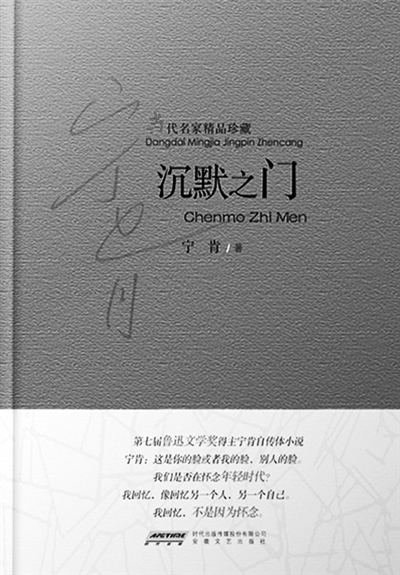近日,第7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宁肯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沉默之门》出版。《沉默之门》讲述了一个新时期“零余者”的成长经历和出路选择。主人公李慢少年时期结识了精神导师倪先生奠定了传统知识分子孤高出世的精神内核。青年时他与身份成谜的女子唐漓恋爱失败,在失恋和失业的双重压力下精神崩溃,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渐渐产生了入世之心。出院后他步入社会历练,在见识了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后,他重建了自己作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完成了知识分子的坚守和传承。
《沉默之门》的价值不仅是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面临时代变革时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纠结与坚守,更在于作者用充满诗意的表述塑造出了一个新时期的“零余者”的形象。小说中弥漫着的诗意的表达,使《沉默之门》展现了与普通自传体小说不同的美学风格,无论是诗歌的穿插引用还是诗歌语言的运用都使小说与现实之间产生了疏离。这种疏离感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很难在心理上与主人公产生共情,更突显了李慢的孤独和“零余”。 《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是小说中反复出现一首诗,这首象征意味很强、略带神秘色彩的现代诗奠定了小说的基调。从一开始,李慢就与社会格格不入,他的个人修养很高,趣味又很小众,在社会巨大的变革下,他如同观察乌鸫的人,用十三种方式津津有味地干着在别人看来无聊的事情。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失恋和失业的双重打击,逼着李慢必须融入社会才能生存。李慢尝试了,失败了,他在大雪中吟诵起了海子,他与海子一样被“切为两半”,他疯了。至此,一个新时期的“零余者”的形象已经立住了。
《沉默之门》的文本结构也是开放式的,小说既可以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故事,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面临的不同选择和不同结局。小说的第一章“长街”是倒叙,第二章“唐漓”才是时间逻辑上的第一章,这两章交代了李慢成为“零余者”的原因。第三章“医生”、第四章“南城”、第五章“幸福”,这三章如同小说的三个不同的结局,探讨了这个新时期的“零余者”是否还有出路。于是精神病院的杜梅医生、李大头,《眼镜报》的知识分子O、W、T等人轮番上场了。小说看似在以李慢的视角描写与这些人相处的经历和这些人的结局,其实暗喻了李慢的选择与结局。“医生”中李大头的结局暗喻了李慢无法入世彻底与社会脱节后的结局;“南城”中《眼镜报》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又暗喻了李慢入世成功后的状态;而“幸福”中李慢与杜梅医生结婚,获得了幸福,则是作者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找到的一条出路——与自己和解、与社会和解,知世故而不世故,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找到平衡,获得“诗意地栖居”。
一部优秀的小说一定能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沉默之门》做到了,有人说它是寓言,有人说它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其实,读者不妨也学学李慢,用十三种方式来解读《沉默之门》,或许会得到不一样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