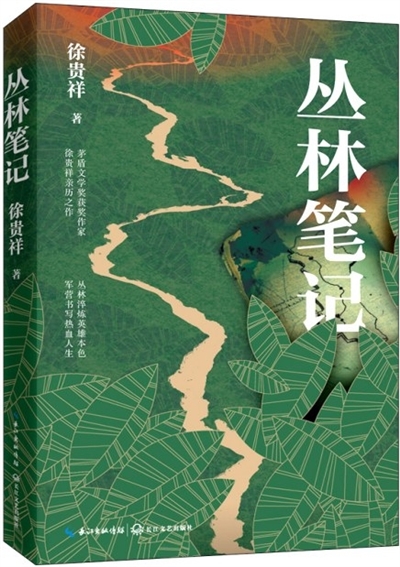○李 艳
作为“正面强攻战争文学的重型坦克”,作家徐贵祥的创作历程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学史诗。从长篇巨著到中篇佳作,他始终以冷峻深邃的历史意识与滚烫炙热的生命体验,仰望历史的天空,构筑着独属于他的军事文学堡垒。他的中篇小说集《丛林笔记》是其向自己的青春岁月致敬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与强烈的现实感。《丛林笔记》收录的《丛林笔记》和《好汉楼》两个中篇,穿梭于他的戍边经历与从文之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起一座连通战争记忆与和平岁月的精神桥梁。
与长篇小说中的宏大叙事、多声部的全景叙事不同的是,徐贵祥的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凝练为单线、近身的细腻描绘,即“微观体感,中观套路,宏观战略”。他采用个体叙事,以小见大,侧重于个体的微观体验与心理变化,从中展现历史的厚重感与沧桑感,思索信仰与生死的终极意义。《丛林笔记》塑造的是一位“成长型英雄”,小说以新兵杜二三的限制性视角,将读者直接带入生死拼杀的战场,直面战争的惊心动魄与血腥残酷,让人体会到战争中生命的无常与脆弱。《好汉楼》以毕得富的文学视角来捕捉军营中的生活质感与日常细节,在日常叙事中完成了从军营到文苑的自然过渡,和平年代一个青年军人的文学梦由此变得丰富而立体。
青春是奔放、昂扬、乐观的,徐贵祥的性格则是“风趣幽默、大大咧咧而又粗中有细”,这样一位“顽童”式的作家的“致青春”力作,其总体风格也呈现出他的小说一贯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特质。小说中对战场场景的还原、战略战术的部署,对军队人员工作与生活的描绘,都来源于其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真切感悟,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基本特征。《丛林笔记》中,出征之前,“我”还心存侥幸,认为仗打不起来,还写了“马革裹尸”“不破楼兰誓不还”“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之类的“请战书”,直到步入战场,部队遭遇敌人的火箭弹袭击,“第三发火箭弹在距我不到三十米的地方爆炸,强大的气流将我冲了一个趔趄,只觉得肩膀被砸了一下,顺手一扯,我的天哪,是一只手,一只血淋淋的手,一只露着骨茬的手,像烧焦的熊掌,几个手指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这惨烈直白的场面,直接炸蒙了“我”,“我像箭一样离开炮阵地,像野兽一样狂奔……我就是想跑,想离开这个血肉横飞的地方,离开战场,找一个不会挨火箭弹的地方藏起来,藏到山洞里。”“我忘记了海燕,忘记了海鸥,忘记了海鸭,我只想成为腾云驾雾的孙悟空。”这是一幕现实版的“残酷青春”。即便如此,镇定下来之后,在险象环生的战场上,经历了“搜山战斗”“间瞄射击”“澜溪长形高地战斗”等,目睹了身边的战友负伤甚至牺牲,“我”逐步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开始思索责任与担当、自由与纪律、生与死等问题,实现了从普通青年到合格战士的转变。也回应了小说开头,尚副政委给我们作战争动员报告时,刻在我心里的那句话:“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对《牛虻》《海燕》的引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化用等,为小说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与理想主义的光辉。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集与徐贵祥以往小说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对军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重新体认。这部小说集将笔墨聚焦于小人物的成长,重新校准与定义“英雄主义”。英雄既能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也能在笔墨耕耘甚至平凡生活中发挥力量。《丛林笔记》中杜二三的三等功与军校录取通知书是军人凭本事挣来的高光时刻;《好汉楼》中毕得富对一篇稿件成功地校正、以笔墨写春秋是文学传承与英雄谱系的紧密勾连,也是和平年代军人的另一种荣光。
从《丛林笔记》到《好汉楼》,两个中篇一武一文,围绕着军人与战争、和平的主题展开叙事,堪称军旅文学的精神双璧。文如其人,徐贵祥本人也恰如坚毅的军人精神的守望者,既护持战争记忆之火种不灭,亦耕耘和平年代的文学新苗,终在军旅文学的铿锵行板中吟哦出一曲别样的青春之歌,在历史与现实的经纬交织处铸就出兼具思想锐度与艺术肌理的军旅精神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