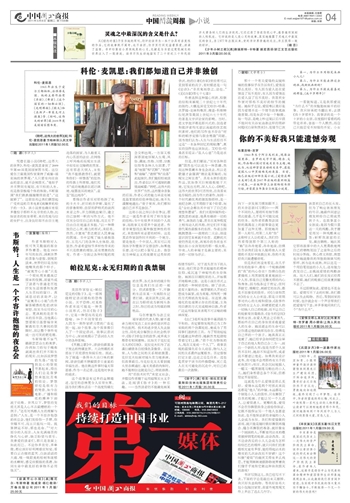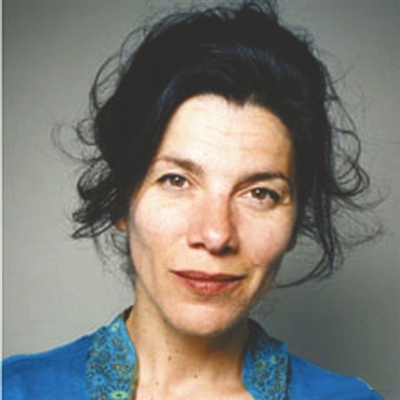1960年生于阿尔及利亚,现居法国里昂。吉罗的文字干脆、精准、尖锐,作品都以探讨家庭关系为主题,她认为,从这种紧密互动的关系中,最能窥探人心中黑暗难见的角落。目前,她已出版过四部长篇小说,《爱情没那么美好》是其2007年出版的最新短篇小说集,一出版即登上法国畅销书排行榜,并荣获当年龚古尔短篇小说奖。
○谢琼(文学博士)
那十一个有关爱情的尖锐疼痛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爱情没那么美好。有人因为爱人还在爱情没了而不美好,有人因为爱情还在爱人没了而不美好。我喜欢女作家对那些不美好的细节的捕捉。她似乎在说,爱情难以美好是因为爱情不是一个情节故事或浪漫喜剧,而是生活中每一个触摸、每一句话,是晚上吵过架以后早晨不能问有关浴室油漆这样的琐碎问题(《白昼和黑夜》),是情节已该向下一步发展习惯却跟不上的无奈悲哀(《习惯》)——两个不同的人,要将所有细节都彼此接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作者那典型法国腔的高高在上的叙事姿态更加重了这种无情。即使她用第一人称写,用第二人称“你”去称呼主人公的爱人,我们仍然看得到那个第三人称的“她”在冷冷地看,冷冷地说,仿佛在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将他人从爱情的不美好中拯救出来,你的不美好我只能遗憾旁观。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在几乎所有的故事中,都有一个轮廓清晰的“我”的内心存在?仿佛白色的素描纸上用黑钢笔重重地画出一个人形,那是自己完整无瑕的内心和身体,因为线条过于肯定,任何弄脏它、模糊它、刺破它的东西,都是不容接受的毁形。对《白昼和黑夜》的女主人公来说,那是日常琐事对内心的无视和侵蚀。《故事终结》的女主人公,则硬要把爱人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轮廓,而不让自己的轮廓有丝毫修改。《恰当的空间》里的女孩,在爱人死去之后很久,都始终在自己的身体里承载着爱人的生命。她说逝去的生命可以让你透过他的缺席而存在,仿佛是自己怀的一个孩子。她真真正正地爱了,她已经学会如何把完全异于自己的他人和自己合二为一,画出一个新的人形;但是当那个人突然不在时,她却不知道如何,或者说不愿意让他走。如果我来设计此书,我可能不会用那些有关手的彩色图片;相反,我会沉闷地插入一幅又一幅黑钢笔勾勒出的小人儿,她们身形姿态各个不同,但都坚定不容侵犯。
这就是为什么爱情没那么美好。爱情永远是两个对彼此来说还都是“他人”的冲撞,永远都是一个钢笔小人儿的毁形,只有撕裂了自我的轮廓,才能让另一个人进入,让爱情进入。更糟的是,爱情不会在你撕裂自身之前给你保证,它既不能保证另一个他人也愿意如此,也不能保证新的幸福的小人儿会成为永恒。我们和爱情做的游戏,就只能是随时做好撕裂再缝合、缝合再撕裂的准备,就好像有一个画画的人,不断要用沾水的橡皮擦掉钢笔的轮廓,涂涂改改。且不论涂改后的小人儿会成为怎样结结巴巴的模样,就只问我们的素描纸究竟有多厚,能经得起沾水的橡皮的几次涂改而不穿破?这个叫做“爱情”的幽灵又得有多么残忍,才能笑眯眯地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傻乎乎地和它做这种自我毁灭的游戏?
书评写到这儿,我已经写不下去,下面的字总是敲出来又擦掉。我只好先去购物。等我好容易大包小包拖回家里,却意外地发现文件上多出了这么几行字:
第一, 为什么不用铅笔来画小人儿?
第二, 为什么不能丢掉过去的画,找新纸画新的?
第三, 为什么不提我最喜欢的那篇,《我十岁那年》?
一看就知道,又是我那爱说“为什么不”的双胞胎妹妹干的好事。我只好再把书翻出来,去读《我十岁那年》。故事讲的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在度假时看着妈妈带走弟弟,爸爸一个人默然,而自己只能忍受不知情的不安。小女孩喜欢自己的长头发,但为了响应爸爸理发的号召,她最终同意让理发师给自己剪成男孩子头。在故事里小女孩说:是因为假日里这一天的残酷,我才接受用另一种残酷来应答:斩断我浓密的长发,做出牺牲。她比其它那些故事中的大人更勇敢地用自己的牺牲划出了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分界线。我心疼又欣慰,我想也许她就像我的双胞胎妹妹写的那样,因为还未成熟,所以还是一个用铅笔划出的小人儿,还有能力改变自己,去挑战爱情的残酷游戏。而大人们,她们的长发已经再不愿剪,她们的轮廓已经浓重到擦不去了。
不过即便如此,爱情也不是全部。爱情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先去购物。然后,等到回家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个声音帮我们把爱情写下去,并多事地问我们几个“为什么不”。
《爱情没那么美好》[法]布里吉特·吉罗著 周小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