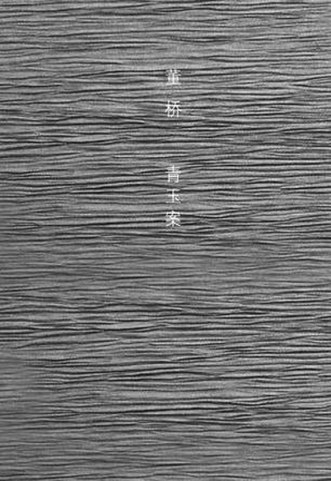○冯 磊(书评人)
一个在天津报界供职的朋友,听说我最近在读董桥,说了一段很可爱的话。他说:“董桥的文字看起来是清新的,读起来却如吃红烧肉。”这评价颇为地道,就像当年冯苓植笔下写汤褪驴一样,老汤的味儿浓重。
手头这两本董桥的文字,一本是《记得》,还有一本是《青玉案》。后者,取自于宋人贺铸的一首词。贺铸写道:“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幅散淡的宋人笔墨。董桥引用这首词,专用了一个页码。标点,却采用了古人的圈识,而非今天的逗号句号。我觉得很好。大凡古诗古词,断句用今天的标点符号,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这,是一个读书读到迂腐的人才有的怪想法吧。
这两本书,有时在案头。有时如厕,也被我带进厕所里去。不到半个月,竟然读了大半。古人论读书,有“枕边书”的称谓。董先生这两本,却被我作了厕边之书。缘分如此,希望老先生不要见怪才是。
董桥记得什么?或者说,董桥都记了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说一说的问题。
这两本小书,是广西师大版“董桥文存”的一部分。论内容,要么是文坛旧事,要么就是大谈收藏的欢欣。怀旧是永远的时髦。不然,张爱玲在今天不会拥有如此多的粉丝。前几年翁美玲也热了一把,缘故,同样也是怀旧。董桥老先生似乎对此颇有心得,他的文字虽短,却无不是在讲故事。
董桥要给我们讲一讲在伦敦张太太的精舍里吃面条的旧事,而且小心翼翼地告诉你,面条有N种煮法,颇有孔乙己先生告知周遭一群小屁孩“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味道。只是,面对这种老人,你感激还来不及,怎么会讥讽与嘲笑他呢?再不然,老先生会得意地告诉你,他某年月日曾经搜罗来了梁启超先生的遗墨,或者溥雪斋的旧画。尤其是,他发现了爱新觉罗家某位姑娘的旧作,而这位姑娘长期以来是被外界忽视的。一个喋喋不休的老文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往事。视野所及,忽而是本港,忽而是英国伦敦或者美国纽约。就这样地聊来聊去,你或者突然就明白了一些人情世故,文坛苦乐。
相对于内地的文化老人,董桥自然幸运很多。他以及他们的价值,在于能够时刻提醒我们传统与现代之间维系的重要。他的尤其可贵之处,在于以个体的经验保存了旧时代风物与人文的风度与记忆。董桥是富贵的,我说的不仅仅是文字。董桥是幸运的,我说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遇与遭际,还有的是他的文字。
我早年曾经读到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份杂志,提到有大陆文人访问香港与新加坡,归来之后写道,“香港是文化沙漠”。当时心里是认同的。但今天看来,香港有金庸的武侠,有董桥的随笔,还有红遍全球的武打片……怎么能说是文化沙漠呢?在香港,董桥就这么平静地生活着。当内地大批人在声嘶力竭的候,他却在书房里静静地把玩自己手头的文字。在大陆,文化老人故去之后,现状似乎也是沙漠的一种了。但香港,以及海外,仍然还有更多的优雅和风趣。据此,我找不到更多值得内地文人骄傲的东西。
作为读者,或许我仍然不能完全读懂董桥。但,这并不影响我在厕所里或者枕头边静静地阅读他的文字。就像我确实不懂如何弹奏钢琴,却仍然喜欢理查德和肖邦一样。礼失求诸于野,这是古人的见识。了解文人的雅致与文化的风骚,到董桥或者董桥以外的地区与异国他乡,或许更好。
此桥,非彼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