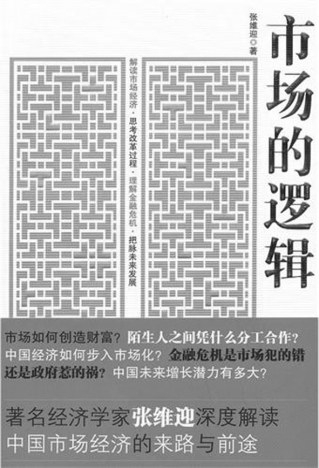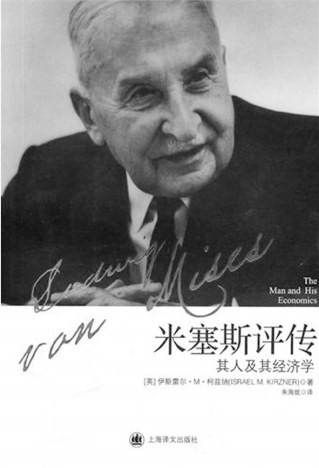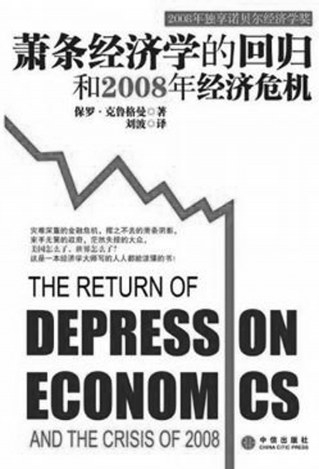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的主要贡献是:创立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人们通常把持该主张的经济学家称为“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的主要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惊世骇俗之处,在于打破了此前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的信条:自由放任、不受干预的市场,能够自动地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从此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就一直是经济学中两种并存的思潮。凯恩斯最著名的继承者就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他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旗手,其《经济学》(1948年第1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机结合,为美国混合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提供理论支撑。
当然,有人继续沿着古典经济学的路径发展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最有名的继承者当属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其领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旷日持久,是因为当时的美联储过分谨慎,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有新奥地利学派,如米塞斯,据说新奥地利学派的几个学者,准确地预报了1929年金融危机的时间,他们认为,金融危机不过是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正常调整。
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刺激计划,似乎暂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刺激计划所带来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他们开始强烈呼吁政府应该开始停止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理由就是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有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酿成更严重的祸害,即政府失灵。例如,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总之,两派学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都纷纷推出新著,各自从自己的角度为金融危机总结经验教训。虽然有时不免各执一词,但多数经济学家还是认为:市场的作用是基本的,应该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政府的干预有时也是必要的,因为市场也存在缺陷。
○何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博士)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美国的就业率依旧低迷,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时有发生,但总体而言,在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的强烈的经济刺激计划影响之下,全球经济基本避免了二次探底的风险,金融危机的阴霾似乎正在逐渐散淡。那么,再回过头来看看金融危机的滥觞原因、应对策略,梳理一下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会更加清晰,更加理性。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实施过于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其新著《市场的逻辑》中指出,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解决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干预,而是让市场自发调节。从理论渊源上看,他所归结的原因来自于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奥地利学派。与名扬天下的具有强烈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凯恩斯主义不同,奥地利学派作为鼓吹自由主义经济的代表之一,长期处于经济学界的边缘状态,并被决策者和社会公众所忽略,尽管该学派也产生过像米塞斯和哈耶克这样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
解决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干预,而是让市场自发调节
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有着三个明显区别。第一,在市场的本质上,它认为在不确定和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市场是唯一有效率的体制,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第二,货币非中性。通常情况下,在经济中发生大的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高时,一般价格水平应有相应下降才对。如果货币当局试图维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就可能将过多的货币注入经济体。一旦“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多的商品”,就会促使经济扩张加剧、繁荣过度,直至出现泡沫和危机。对此原理,国内三年前出版的米塞斯的专著《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和新近出版的《米塞斯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给予了专门分析。第三,在价格变化上,它不是关注一般价格指数如CPI、PPI的稳定,而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尤其是利率和资本品价格的变化。例如,美国1870~1879年的价格水平年均下降1.8%。按照凯氏理论,经济将陷入收缩和萧条,但实际上这是美国历史上增长的黄金时期。这就意味着,不能一看到物价水平下降,就立即注入货币。因此,在政策实践上,奥利地学派坚持最彻底的放任自由主义,反对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以各种理由干预经济。
不仅如此,在张维迎和奥地利学派看来,经济萧条不是由于市场有效需要不足,而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这恰恰有助于解决经济中的问题。对于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米塞斯和哈耶克都曾预测到了,尽管没有指出准确时间。1962年,奥利地学派学者罗斯巴德在其出版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中,指出30年代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就是美联储当时扩张货币政策和低利率,并声称找到了切实的证据。根据他们的理论,当时美国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美联储把利率定得过低,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促使企业家盲目投资于重工业和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而流动性过剩引致股票市场逐渐生成泡沫,并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全面带动原材料、工资价格上涨和投资成本上升。在政府的扩张性政策一旦无法持续时,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原有资金沉淀在固定资产中,由于无法变现而出现短缺,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也就到来了!因此,任何一个经济体中,人为造成的大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奥地利学派学者也事先做出了预警。《美元大崩溃》的作者彼得·希夫在2006年的一次电视谈话中预测美国要出大问题。基于这些事实,张维迎在书中乐观地预测,“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利地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平心而论,张维迎和奥地利学派的看法不无道理,如果政府不顾客观实际情况,过多干预经济或者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这样的经济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市场自由就是万能的吗?从经济史来看,自从亚当·斯密《国富论》首次发现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巨大作用后,西方社会一直主张经济自由政策,迷信经济本身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能力。直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之后,主张“有形之手”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才登上历史舞台。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涨”的怪圈后,凯恩斯主义又黯然退场。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自由主义又开始盛行——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潮和政策实践,似乎就像一直在坐历史的跷跷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而与它们相伴相随的市场与政府、自由与干预的二元对立思维和话语体系也盛行了数百年。然而,在不同的现实经济体系中,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是难以发挥积极、理性、健康的作用的。因为,面对信用匮乏、法治混乱、裙带经济、腐败猖獗、公共服务缺失,市场又将何为,又能何为?面对人性的天然趋利、创造性激情的枯竭、自主创新能力的衰弱、企业自生能力的匮乏、民间经济活力的枯萎,政府又将何为,又能何为?此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每当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总有强烈的声音呼吁政府出面干预,给予包括利益集团在内的各种经济力量以支持;一旦危机过后,市场万能的观点又甚嚣尘上,政府的任何措施又似乎成为干预市场经济的破坏行为。这是否也是一个现实的悖论?
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而不是国家财富
在《市场的逻辑》中,张维迎还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及其未来发展举措。作为国内“双轨制”最早的提出者,他指出1988年到1992年我国经历的价格闯关和开放过程,恰恰是因为“政策能够顺其自然,将自发的力量变成自觉政策,把改革变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席话一方面表明“双轨制”作为一种自发性的过渡性制度形态,减少了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和内在阻力,为弥合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做出了独特贡献。另一方面由此可知,市场经济的形成也不是天然的,而是一个自发性和自觉性兼具、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同一的历史过程。在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没有建立、宏观经济环境不够完善之前,必然存在一个政府干预、引导甚至“试错”的过程。
在张维迎看来,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采取如下措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企业加强自身调整,增强核心能力。应该说,这几条措施是切乎实际的。其一,市场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调整和修复的动态过程。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更需要以此来不断保持制度创新的动力和活力。其二,面对宏观经济内外失衡更加严重,巨大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客观上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是必然的制度选择。其三,“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wealth of nation)的,而不是国家财富(wealth of state)的。” 尽管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如果不能够从制度设计上改变初次分配的调节力量过强、二次和三次分配的调节能力过弱,全面彻底地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水平差距日益扩大的局面,中国也将堕入拉美国家曾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企业的自生能力和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若不强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将是一句空话。要正确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共同作用,而不是人为地将市场和政府相互割裂或者对立。
面对70多年前的大萧条,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说“不论是福还是祸,带来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面对3年多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张五常在《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中说,“从减低交易或社会费用的角度衡量,有些事市场较有效率,另一些政府较有效率”。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说,“妨碍世界繁荣的重大结构性障碍只有一样,就是那些充斥在人类头脑里的陈旧教条”。面对日新常变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应该超越关于市场与政府、自由与干预的二元对立思维和话语视角,正确地发挥“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共同作用,努力实现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之间的平衡。这才是求实、理性、务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