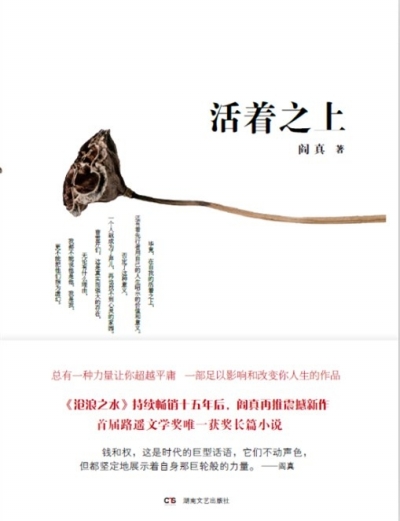阎真最新小说《活着之上》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直面人生的勇气,更在于它在直面中思考,并尖锐地提出一系列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精神图像,引起人们对自身庸碌生活的质疑和不满,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在阎真看来,在金钱支配下所造成畸形的灵魂,道德的沦丧,以及风气的败坏,等等,都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的。而这些丑陋和阴暗的东西之所以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中,是因为人的欲望过于强大,但欲望不是推动活着的唯一动力,与欲望相对的良知也有着强大的活力。
在许多人看来,生存不是问题。但生存不是活命,而是必须守护“活着”的尊严和心灵的信仰。这原本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生活常识,但这种常识却被强大的现实尖锐地撕裂,以至于你要维护这种常识,需要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否则,你就有可能倒在常识的背面,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小说中,聂志远报考博士生,与蒙天舒一起竞争,“别的我比不起他,考试我也考不过吗”?然而,命运就是这么戏弄,聂志远被刷下来,而蒙天舒考取了。“我的外语比他多了11分,可专业竟比他少了15分。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自己的命运似乎已被别人精心设计。”很少读书的蒙天舒通过送礼物送钱等手段,居然弄了一个优秀博士论文。蒙天舒坚信“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是他的生存哲学。他认为“现在是做活学问的时代。死学问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死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现实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像昆得拉笔下的生命,重得让你无法承受。更讽刺的还是:蒙天舒后来当上了院长助理,而聂志远在经历种种折腾后,竟最终成了他的部下。
这真是一种绝望。可贵的是,深陷绝望的聂志远并没有沉沦,更没有倒下,而是被内在的绝望所吸引,为自己的执着所感动。因而他超越了绝望,或者说,比绝望更绝望。有了这种心态,也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这是一种痛苦的升华,也是自我的审视。小说中,这种不安定因素十分突出,造成自我和现实的空前对质,不仅表现在文本中,也表现在作者和读者中,这种现实的残酷与内心信念之间的敌对,是整个社会和个体生命紧张对质的文化镜像。这种镜像不断被小说一个个生动的细节所打破,一次又一次地发出现代人在物质世界的诱惑下灵魂挣扎和哭泣的声音。
阎真对人性的黑暗有着最深切的体验,作为现实生活的反省者和心灵世界的写实者,他揭示了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揭示了隐藏在人表象世界后的某种本质。在小说的最后,阎真不无深情地写道:“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的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