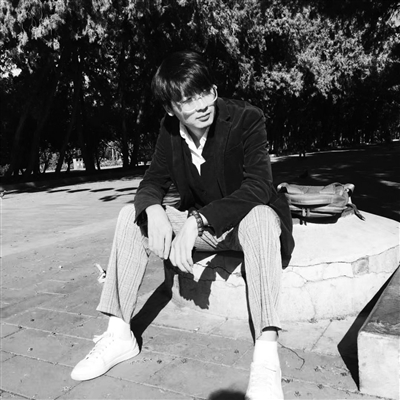■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
小说《夜游神》,孙一圣写了2次。第一次写了3万字,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题目”,于是整个废掉,重头写起。就像《邪不压正》里,姜文的一句台词:“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的这顿饺子。”孙一圣想出了一个题目,为它写了一篇小说。
《夜游神》属于主题性小说。孙一圣认为最好的主题性小说是《活着》。余华要写“活着”,写的却是亲人接连死去。“如果所有的亲人最后都活着,那不叫活着,那叫生活。”孙一圣接着说:“所以主题的选择很重要。”由此,《夜游神》也成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
只能从身边写起
《夜游神》的开头,孙一圣摘了3句话。这3句话摞在一起,占了半页纸。第一句出自契诃夫:“一个疯人认为自己是个鬼魂,一到深夜就到处走动。”第二句出自道教《净心神咒》:“三魂永久,魄无丧倾。”第三句出自佛教《楞严经》:“夜见灯光,别有圆影。”孙一圣认为第一句并不突兀,因为“契诃夫”是一种“文学宗教”。
小说里,毛毛是曹县一中的数学老师。她有洁癖,课前课后都要洗手,哪怕“洗掉一层皮也不在乎”。毛毛从不请假,只迟到过一次——厕所门关了,要出去只能拉门,而拉门后又得洗手,陷入死循环。于是,她迟到了整整一节课。直到下课铃响,有人开门,她才侧身闪出。写完毛毛的开场,孙一圣意识到,这是一个困在洁癖里的人,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事实上,这个细节是孙一圣的亲身经历。他在商场的卫生间里,自己的纸巾用完了,卫生间连厕纸也没了。面对关住的门,他张着手,指尖滴着水,等待推门而入的人。《夜游神》里的主角“我”,是毛毛的学生。课上,毛毛说:“人类发明十进制,因为我们只有十根手指。”听到这里,“我”甚至觉着,“人类所有的秘密都在这十根手指里”。
这是孙一圣想写的。“为什么是十进制,因为古代只能掰着手指头数,只能数到10。”孙一圣张开双手,他说:“如果人类只有9根手指,那么计数法就会是九进制。”他没有查过资料,但坚信“这个逻辑是通的”。“每个人都有过一些奇怪的想法,看起来很有道理,只是有的人说出来了,有人的没说出来。”他想把它写下来。
真实的想法包括:手机调到静音以后,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拿到手里,手机变轻了,好像失掉了重量;出门以后,总会疑心没锁门,不论走出多远,还是会折回检查,结果发现门锁了。比如坐车,如果两个人正在吵架,第一下猛拽安全带是拽不出来的,需要慢慢拉才能拉出来。还有一件刚刚发生在孙一圣身上的事,他下楼时踩过了每一级台阶,最后一步迈了2级。他折了回去,把最后一级台阶踩了一遍。
《日游神》是第四篇小说,讲了一对父子的故事。小说灵感来自于一则社会新闻,一名警察为独居老太太“驱鬼”。这则新闻具有匪夷所思的成分:“驱鬼”是道士干的事,然而她却向警察求助,最终得到了安慰。这是两个时代的黏合:“驱鬼”是早年迷信思想的残余,而报警则是现代社会“有困难找警察”的理念渗透。这个真实的新闻击中了孙一圣,他看到了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个看似矛盾的事件,拆解开看,却合情合理。
《还乡》里,“我”老是梦见死去的亲人,于是去算命,连掷了六回硬币。算完命,乡村医生告诉“我”,不是鬼的问题,该拜神了。临走前,乡医开了药——阿普唑仑,一种用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失眠,抗惊恐的药。孙一圣把两个熟悉的部分捏在一起:表面是求神问佛,而核心是现代医学。他见过赤脚医生开药,开的是护身符,让人放到枕头下,然而里面是有安神功效的中草药。
孙一圣第一次见识到日常生活的诡谲,是在上大学时乘坐的公交车上。学校放假,孙一圣乘公交车去火车站,半程上来一个人,他只有半张脸,另半张被烧没了。见过半边触目惊心的脸后,惊恐使他不敢再看第二眼。于是,他只能看向车厢里的其他人。下车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记住了所有人的脸和表情。在此之前,他乘过上百次公交车,却对这些完好的、正常的脸熟视无睹。
他只能从身边写起,写一点深深困扰自己的东西,写出生活中被忽视的一面。自序中,他写道:“有时候我们总觉着一天过于漫长,但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却觉得一辈子不过短短一瞬。”孙一圣解释,回忆过去几十年,人们想起的都是重大事件,比如出生、上大学、结婚生子,老人去世,所以常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孙一圣想让时间变得坚硬,让“一天”如同一根竹签,穿透“一生”这根烤肠。
写小说需要时刻警惕
《还乡》是在卫生间写出来的。2017年,孙一圣在北京,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冬天冷,暖气的热量微弱,不大的出租屋,只有床是热的。在床上写,进度慢,“一闭眼就睡着了”。屋里有一张简易长桌,是孙一圣在宜家花99元买的,刚好能塞进卫生间。把浴霸打开,他坐在马桶盖上,桌子顶着胸膛,坐得笔直地开始写。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足够暖和,又不至于睡去。其间,他坐坏了一个马桶盖,即便心疼,也只能再买一个新的。
“我是贴着小说写的,有时甚至把半个身子泡在小说里,以至于不得不写一段歇一段,透口气。”孙一圣见过一张画,画的是卡夫卡半截身子埋在文字里。他想到了自己写作的状态,就像水涨到胸口,大口大口喘着气,抵着水往前走。同时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稍一用力,就踩破了稿纸。
孙一圣把写小说比作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保持“真”的状态很难,因为廉价的道理和情感容易趁虚而入,让语言陷入虚假的泥沼。写《山海》时,他感到“很多东西蜂拥而来,特别是生活四处蔓延,能够隐约体会到一种宽度”。他写了大片大片的景物,试图让文字漫过小说的边界。未来,他想写一部没有人的小说,只有景物。
“你会发现,只要去写一个执拗的人,很容易出故事,就像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孙一圣讲到了这篇经典小说。贵族小姐艾米丽发现,爱人无意与自己成婚,便将其毒杀,和尸骨同床共枕40年。他在小说《日游神》里也写了一个“执拗型”人物。辅警马贼在宁三秀家“驱鬼”,他没有资格配枪,只能用擀面杖敲了三下铁锅,模拟枪响。三声“枪响”过后,他突然理解了父亲。
“小说过于理想化了,现实世界里不会这样。”他观察过很多对父子,多数是沉默的,彼此交流很少,各过各的。以前类似的执拗型人物,孙一圣经常写,现在会尽量避免。一方面,因为执拗型人物缺乏普遍性;另一方面,因为这一类人物容易出故事,“有偷懒的嫌疑”。《夜游神》里,毛毛有双重身份:白天是数学教师,晚上则走进不同的宾馆。在警局录笔录时,她说出了真相:她有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地不能拖,只能跪在地上擦,电饭锅内胆里有一滴水,母亲就会尖叫,甚至连垃圾桶里的垃圾都要摆整齐。她不想待在家里,只能出门。
在高压的亲子关系中,如果没法扛住,孩子就会“断掉”。在毛毛的成长过程中,有过许多这样的时刻。面对死亡,她恐惧,于是后退了一步。抛开性别来看,毛毛也是小镇青年的缩影,他们在故乡痛苦、挣扎,却无法全然离开。孙一圣回忆起家乡曹县,和许多的小镇一样,街边是棋牌室、KTV、盲人按摩、洗脚店,很多人在牌桌上打发时间。他看到的是,小镇人无处安放的精神需求。“在一线城市,你可以看话剧、歌剧、球赛,去博物馆、游乐场。但在小镇,只能打牌、打麻将,没有太多选择。”
“冬至早过了,北京还没下过一场雪。我去买水,回来路上平白跌了一跤,水桶摔破了,水都洒掉了。我因此告假,与妻回到久违的故乡。”这是《还乡》的开头,通篇是“妻”,而不是“妻子”。每写完一大段,孙一圣会停下来读几遍。他特地选了个单字。“用‘妻子’会有棱角,就像在路上出现了一块砖,会把人绊倒、磕伤。‘妻’也有起伏,但这个起伏是圆滑的。”孙一圣解释完后问:“你能感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