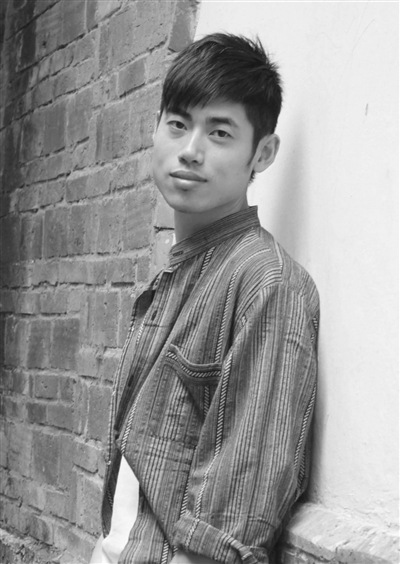作为凤凰的化身,“朱雀”是南京的地标之一,葛亮选择《朱雀》作为叙述南京的书名,显然着眼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和沧桑。故事从一位苏格兰华裔青年南京留学,回乡寻根,在秦淮河畔邂逅了一位女子开始,由此引生了一个家族三个世代的传奇。葛亮从民国一直写到千禧年,无论是时势动荡,还是家族历史,或是交织的个人爱恨情仇,家园和故土,成为他咏叹的主旋律。
正如他所说,“南京是我的家城,我用一个游走者的角度去看中国,去审视,去想象。”因为没有像父辈一样能亲历事实,故事而只能靠想象,也因此,用年轻人的视角来看的故事便呈现得更为自由。虽然如此,在年轻人的故事之外,血脉传承却让这个古典气韵的南京城显得充满宿命感。
大学时代,葛亮就萌发了为南京说故事的念头,一直到30岁完成了这本书。5年的创作时间和更长时间的沉淀过程,让他从容完成了这部小说。而触动他动笔写作的,是南京夫子庙遭遇的工业化文化危机。有一年,他突然注意到秦淮河边的老字号六凤居的楼下出现巨大的金黄色M,因为这家老字号难以维持经营,不得不把楼下租给了麦当劳。那一刹那触痛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传人,但当你发现这个城市也在默默无奈地变化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如果有一天这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那唯有一个方式,就是在纸上留下它。”于是,在历史小说之外,《朱雀》也成为了一本关于南京的人文地理的小说,为年轻读者提供众多审视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受访人:葛 亮(作家) □采访人:海 兵(商报特约记者)
《朱雀》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书写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你的故事中有西方的思维,但你骨子里有很传统的东西,在写作中没有矛盾吗?
■虽然我写的是南京,但是写作的格局是全球化的,里面涉及到很多外来的元素,包括爱情,异国恋成为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写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为什么会出现?我觉得核心的部分在于,我可能想表达这种碰撞,所以必须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和外来的元素同时出现,同时交融,甚至于同时磨砺跟磨合。
□《朱雀》里抛给自己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一个年轻人对于历史的态度。父辈的作家更多地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我们是被父辈见证的这些对象的一个接受者。其实我们也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因为没有直接去触碰,反而会呈现出更为自由的状态。比如要重新建构历史,这对年轻人来说真是一个考验。在资料收集工作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情境,让自己进入到其中,有些故事就能自然而然衍发出来。当然最后抽离的感觉会非常苦痛,我写完这部分的时候深切体会到为什么后来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以后,要去选择一条不归路结束她自己的生命。其实历史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实和非真实的区分,像海登·怀特,就讲所有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叙述。从这个角度来说,看你怎么讲、怎么表达,有趣的部分就来自这里。
对文学的敬畏感是写作的两面
□你出自一个书香门第,最初的愿望是文学研究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写作的?
■我20多岁才开始写作,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写作,问题在于小时候的阅读习惯给我树立太高的门槛,让我对文学有特别大的敬畏感。有一天会去写的时候,这些东西会为你积淀很多;但也会导致怕露怯,你可能很晚才做,一旦没有把这种信心积累到一定程度,那这一天的实现就会越来越迟。当然20多岁这个年纪,不算太晚也不会太迟。我当时已经在香港了。
□你到了香港之后才开始写作?
■对。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比较好的文学研究者,之前的阅读习惯让我有很大的兴趣去探究这些作品背后的东西。后来的写作更多是出自于偶然,我写的《七声》在台湾拿了联合文学奖。但这部作品最早只是写给我家人看的,出版以后,有读者说,虽然之前素不相识,但可以在这本书里从一个人的成长轨迹,看到时代的流转和关于我们的故事。
讨论“80后”这个概念不如讨论“独一代”
□你作为文学研究者,如何评价“80后”写作者?
■“80后”作为代际概念唯独在内地如此兴盛,港台几乎不存在。港台的评论界会想为什么不以改革开放为界,他们到现在还要讨论“独一代”,比如涉及到我和我的同类作家的时候,我国台湾的评论者说葛亮是头一代的独生子女,因为这是政府人口政策对整个一代人的命运和心态的影响。“80后”这个概念的意义何在呢?内地一些同辈作家也在质疑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怎么评价韩寒和郭敬明?
■这两个人在年轻人中脱颖而出,并不单纯因为属于“80后”代际概念,他们身上有个人的文化的意义。首先是他们多元的身份,韩寒不但是作家,他被大家更熟知的身份是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是优秀的赛车手。郭敬明除了作家的身份,同时也是优秀的出版人,而且非常成功。恰好他们属于“80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