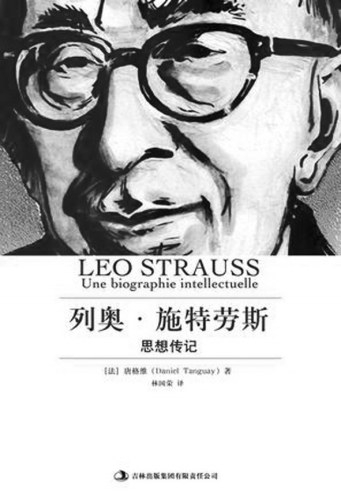○凌小辰(书评人)
1938年,40岁的德国犹太人列奥·斯特劳斯不远万里前往美国,之后在那里定居。斯特劳斯逃离欧洲的原因众所周知,并非他过于厌恶日耳曼,而是纳粹党卫军的枪口指向了犹太人。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美国成为斯特劳斯的避难所,但斯特劳斯却并未热烈地肯定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犹太人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长期以来成为美国主流政治学批评的对象。即使今天也依然是争论的焦点。
因为,斯特劳斯在美国政治学领域的边缘化,与他实际上对美国政治的现实影响很不对称。在美国共和党老布什执政时期,斯特劳斯的弟子们大量地占据着美国政府的许多重要职位,并操纵着政治行为。也正因为这一事实,斯特劳斯甚至被看作是“共和党革命的教父”。在他去世近30年后,美国发生9.11事件,美国政策与斯特劳斯政治学的关系,再次遭遇热议。
站在现代主义的十字路口,斯特劳斯终身忙于质疑和批判现代政治。“现代人与古代人之争这段公案必须重新开审;换言之,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而不带偏见地考虑这种可能性:斯威夫特当年把现代世界比作小人国,而把古典世界比作巨人国,他是对的”。
斯特劳斯大量的意见写在他所阅读的书页边缘和缝隙中,这就是所谓的隐秘写作。这种写作方式、语调和风格,让众多的读者感到震惊。作为评注者,斯特劳斯刻意让自己隐匿或消失在文字的背后,但读者总会时不时地感觉到这些评注的书写者像幽灵一样始终是在场的。不过,如果了解斯特劳斯基本思想的一些原则——“内在于并且仅仅是内在于事物表面的问题,恰恰是事物的心脏。”我们对此就不难理解了。
《斯特劳斯:思想传记》的作者丹尼尔·唐格维解释说:“1935~1938年间,对神启律法的政治解释,对于重新发掘一种隐秘的写作技艺发挥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则哲学承认神启律法的政治功用,从而也有必要采取一种既能保持有益的宗教观点,同时又能暗示出某种哲学真理的写作方式。施特劳斯对直白和隐秘的范畴进行了定义,由此便回应了一种需求,解释了中世纪哲学家们强调哲学和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式。”
斯特劳斯从未直接地呈现自己的政治学意见。对于丹尼尔·唐格维来说,最大的可能,只能是尝试像斯特劳斯理解他自己那样去理解斯特劳斯。也就是说,“我尝试刻画的乃是施特劳斯思想中的本质性直觉,而不是想知道他对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政治哲学传统中其他作家的分析究竟是对还是错”。
尽管斯特劳斯从未大胆立论,但若对其“批注”进行研究,斯特劳斯的主张还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在神学-政治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地跟现代社会的历史潮流唱反调。
在成名作《自然正义与历史》中,基于对以马基亚维里开端的、本质上是“青年造反运动”的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斯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所谓“历史观念”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便是人类开始用“进步还是反动”的区别取代了“好与坏”的区别,却忘了“好与坏”的标准本应逻辑地先于“进步和倒退”的标准。
上世纪60年代,斯特劳斯抛出了两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能让研究者了解到,“老顽固”斯特劳斯如何在现代政治如火如荼的年代,却逆流而动地回到了古代。据斯特劳斯自己的叙述,在1920年代的德国,与卡尔·巴特和弗伦茨·罗森茨威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场神学复兴,打开了斯特劳斯的古代视野,这一影响力巨大的运动,成为他陷入斯宾诺莎情结的最初动力,随着研究的深入,斯特劳斯逐渐加入了反思现代宗教批判的行列。施特劳斯宣称:“自那以后,神学-政治问题就成了我的思索主题。”“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这部研究作品是1925~1928年间在德国写的。作者当时是一个年轻犹太人,生于德国、养于德国,发现自己深陷于神学-政治困境当中”。
由于神学-政治问题的困惑与纠结,斯特劳斯对照现代政治,发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哲学问题是不可能在一种过分狭窄的政治神学观念中进行彻底探究的。
在施特劳斯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对于现代自然权利的抗辩,他建议回归古代自然正当性。对此,唐格维的解释是,“古代和现代就自然权利的本质所发生的争吵,实际上可以溯源于一种更为根本的冲突,此即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冲突”。正是在对这种冲突的不断反思中,斯特劳斯的思想达到了顶峰。也正是这种冲突,使当代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与他在当代的首要敌人之间的分歧变得十分清晰:神学-政治问题,实际上表达了“哲学的追随者”与“律法的追随者”之间永恒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