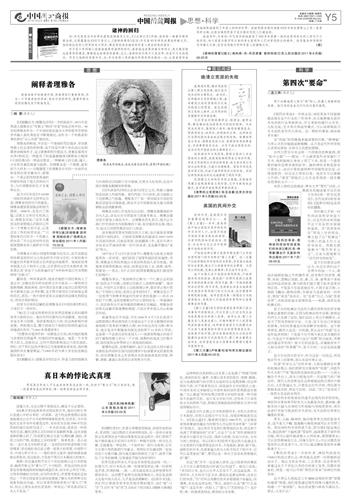那个冷酷地将人视为“物”的人,把握人类脑神经线索。他们仍旧在金光闪闪的仪器外偷笑。
《第四次革命》一书预言说,神经革命不仅能够提高现有各个行业的工作效率,而且能够催生前所未有的新行业和新职业,并且重新构建行业竞争、人际交流、艺术形式和战争模式,可以说将彻底乃至永远改变后代人命运。这一精妙的革命,将由谁来实施?
当“肉脑”的图像越来越清楚的时候,“精神脑”与其心灵的功能就逐渐模糊。这乃是近代科学带给人类看似喜悦、实则令人忧愁的馈赠。
在西方哲学中有这样一个深奥的思维案例,即“缸中之脑”——假设一个人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他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感觉”到他自己正在这里阅读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
当然上面的这段描述,带有太多“现代”词语,古典版本的阐述最早出自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当代电影《骇客帝国》、《盗梦空间》也是类似的翻版。
和牛顿几乎同一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对近代科学的贡献不亚于其在哲学领域的造诣。其“我思故我在”形而上学的预设,建立起了以“机械论”为核心的笛卡尔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把他称为“现代哲学之父”,又有人把他称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笛卡尔的哲思这样认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法窥破缸脑之外的操作者,因为我们的思维、观察、体验、逻辑以及眼、耳、鼻、舌、身、意等各个身体活动和活动场景,都与把我们脑子置于缸中没有任何区别。于是笛卡尔悲哀地宣布,大到宇宙万物,小到蜎飞蠕动,植物动物,有感觉与没感觉的一切存在,皆因“我思”而存在。而“思者”自己,与被“思者世界”,其组成的基本原理则是——机器,或者说是机械式的。
笛卡尔的机械论为近代牛顿自然科学的哲学根基做出重要的贡献,正因为机械论的宇宙观,使得近代西方人充满了自信,他们自信上帝让牛顿降生,正是为了照亮黑暗的宇宙。只是,笛卡尔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却鲜有知晓的。这个困难便是,既然人也是一台机器,那么这台“肉器”怎么运作起来的呢?于是笛卡尔不得不承认有灵魂的存在,可是这个灵魂如何与这台“肉器”结合起来,并驱动肉器运作的呢?笛卡尔的回答是,灵魂就存在于人脑后部的“松果腺”中,笛卡尔的二元论也因此建立。
笛卡尔在西方哲学中,作为过客一闪而过,然而他在科学上的影响,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谓“科学主义”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持有朴素的机械论观点,他们把研究对象视作“机器”,西医外科手术的“尸体”假说即是最好的证明——一旦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只把他当作一具还喘气的尸体对待。现代人的思维也在这种被强迫的合理性中格式化,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是出自科学的,用仪器与数据来说话的,便是可信的。因此,“死亡”也变成了一张医生签名的宣判书。
神经科学的发展依然逃不出现代科学的传统,神经科学家如果不把有关人体最复杂的、最神秘、最根本的大脑与其神经当作细胞与导线管看待,则无法进行实验与假说的学术活动,也无法给信奉者以确凿的答案。
其实,人脑、脑神经、脑功能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远不是几个酶、氨基酸与染色体就可以左右得了的。然而神经科学家热衷于此,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通过拆卸“大脑机器”零部件,搞清楚各个部件的功能,则可以最终搞清楚人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可以回答精神是什么,灵魂又是什么;可以试着改变零部件以改变某个人,亦可以通过操纵零部件来操纵某个人……
《第四次革命》一书的作者、神经科技组织(NIO)的创立者扎克·林奇就是这样一位积极的活动分子。他认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代表着过去几个世纪人类经历的重大变革,而摆在面前的,则是一场可以号称“第四次革命”的神经科技革命。
这不禁让人想起近几年IBM高唱的所谓“智慧的地球”构想,他们是想通过现代网络与通信技术,构建一个“地球脑”。如此的设想与林奇不谋而合。那么,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