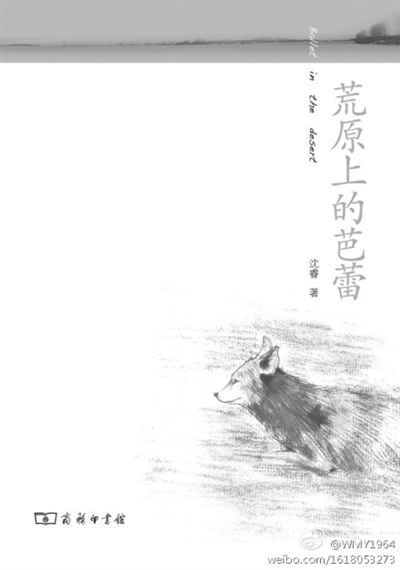从小,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人是猴子变来的,人是高级动物,低级动物的一切似人行为,都是条件反射。从小,生在农村,和动物打交道是生活的必须,没有那么多的意义。
沈睿女士在美国居住十几年了,但在网上,仿佛她就在身边一样,她每次写的有关动物的文章,我都是看的,有时也泛泛酸,想,这些毕竟都是资本主义的动物,哪像我们的初级阶段的动物,生存权尚须努力,哪里还有精力奢谈动物权,有点吃饭饱了的感觉。
沈睿把动物写成是“荒原上的芭蕾”,多么富有诗意,那么动物与人这种动物就是观众和演员的关系了,那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还没有脱离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于是,才有了人对动物的种种观察种种爱戴种种施恩,于是有了动物的权益,不论把动物描述得多么清新自然可怜可爱,都是施恩,这当然是好的一方面,是善良之举;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么,人也可以随时不施恩,可以对动物这样那样,生杀之权仍然在人,所以,小的可以虐待,大的可以杀戮,因为,我是主。由于人把自己当成高级的人已经很久了,特别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把自己当成主人已经很久了,主人可以主宰一切的意识已沁入骨髓,就跟主与仆、阴与阳一样,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了。已经忘了,自己也是动物了。
动物与人这种动物究竟该怎么相处?究竟有什么区别?想得头疼。今早起,终于想明白了:就是人这种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把一身的毛给进化没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天生的带着一身皮毛,终身就一件衣服;而人,就没办法了,赤条条地来,怎么办?冬天冬衣,夏天夏衣,单、夹、薄、厚,样样不能少,冬储夏晒不说,人的高低贵贱都可以从衣着来区别,于是,着衣也有礼制,旧社会,要是穿错了,还得杀头等等,一部中国服装史,十分之九讲的是礼制的,随着大清朝的灭亡,着装的政治问题才解决。
人这种动物与动物的最基本的区别在于没有了毛,于是,才产生了一系列的人的社会问题及自然问题。人毕竟是动物,需要动物的毛,于是,那些有好皮毛的动物算是倒了血霉,虎皮鹿皮貂皮獭皮鱼皮狐狸皮,都得成为人的皮;由于人没有毛,除了穿上动物的皮毛外,还得有遮风避寒之处,于是有建筑史;哪有那么多的皮毛,不能人人都穿上虎皮吧,于是有了纺织史,等等。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与动物有区别历史,一切都是由于人这种动物没有毛。
由于人是没有毛的动物,于是与动物有了区别,渐渐地自认为是高级动物了,就可以主宰动物了,由于人是没毛的动物,为了成为假毛的动物,便有了规制,于是便有高级人和低级人。于是,高级人便可以主宰低级人的命运,就像人可以主宰动物的命运一样。于是,有了反抗、争斗,杀戮,一切都是为了这一身的毛皮。人没有了毛,和动物怎么相处?为了得到更多更好的各种毛,人跟自己怎么相处?
看了沈睿女士的的《荒原上的芭蕾:动物与人散记》,得到了一些启示,那是得等到我们的生活也达了沈睿女士居住地的水平,人们才会善待动物如同善待自己。要么,人就得再进化出一身毛来,与动物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