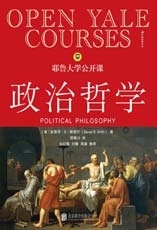施派内部的分歧,本身也依然是政治哲学问题。施特劳斯为了解决现代性危机,因此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种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构成了现代性“洞穴”的对立。
1981年,史蒂芬·B·斯密什从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是列奥·施特劳斯任教近20年的大学,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的师承关系,但我们仍能看出施特劳斯对斯密什的影响颇深。
早在2006年,斯密什就出版过《阅读施特劳斯》(华夏出版社,2012),来回应媒体与学术界对于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的抨击。而这部《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以下简称《政治哲学》),更是接续施特劳斯学派对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重要著作。
在这部书中,斯密什考察了自古及今8位重要的政治哲人,但是他却声称“写作此书是要使它成为一本政治哲学导论,而不是更为常见的政治思想史”。这明确反映出斯密什的写作是政治哲学式的,而非政治思想史的。
然而,斯密什不是施特劳斯,我们既要关注他对于施特劳斯学派观点的继承,也要了解他对政治哲学进一步的思考。套用施特劳斯的说法,我们应该注意这部《政治哲学》的谋篇。
该书后记曾提到,“贯串着这一学派学说的由单一作者书写的政治哲学史一直付诸阙如,这本书一定程度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尽管我们需要承认该书的地位,但也需要看到,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本身,其实也是一部以自然正义/权利为线索的政治哲学史,而且施特劳斯在这部书中首次明确且系统地阐述了施派政治哲学的研究问题。后来,由施特劳斯与克罗普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法律出版社,2010),也只是对于政治哲学问题的深化与补充而已。那么,斯密什的《政治哲学》与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相比有哪些特点呢?这就需要将两部书的内容加以比勘才能得到答案。
通过比对两书目录,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密什在这部《政治哲学》中,省略了对于现代政治危机的检讨。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区别,因为恰恰是对于现代危机的分析,才构成了施特劳斯学派古今之争的议题,也就是说,施派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前提恰恰就在于现代性的政治危机。斯密什将这个问题省略,直接讨论了哲人与城邦的冲突,从而引入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他这样布局的用意何在呢?
我们在后面的阅读中,找到了答案。在处理近代政治思想问题上,斯密什与施特劳斯渐行渐远,虽然他依然保留了施特劳斯部分论断,但是在近代政治哲学的评价上,他显然与施特劳斯有了巨大的分歧。
施特劳斯认为近代政治思想本质上就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而且每次现代性的浪潮都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性的危机。这个观点反映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对于霍布斯与洛克通过自然权利论与传统政治割裂,恰恰代表着第一次现代性的浪潮;卢梭激进的现代性方案代表了第二次现代性的浪潮;而全书前两章描绘的20世纪现代性的危机,则是第三次现代性的浪潮。可以说,施特劳斯描绘的现代性危机,恰恰是近代政治思想与古典政治哲学断裂的结果。
很显然,斯密什放弃了关于现代性批判的框架,在他看来,近代政治思想预示着现代宪政的发展道路,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与传统政治决裂,霍布斯、洛克通过自然权利来构筑现代契约论,为现代宪政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卢梭对公义的分析,则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理论前提。直到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刻画,才真正完成了现代政治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应该说,斯密什以托克维尔结尾,恰恰是呼应了美国现代政治。
如果说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是对施特劳斯现代性危机的通俗解释的话,那么斯密什这后半部讲稿,就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的简化版。这一点也恰恰能够说明,斯密什《政治哲学》与《自然权利与历史》相比为何缺少了现代性危机的部分。
当然斯密什与施特劳斯的分歧,其实也并不稀奇,毕竟“施特劳斯派也分好多种,各自有着诸多不同的兴趣和观点。这样的解释固然成立,但我们还能再深入一步,发现施派内部分歧的关键。也就是说施派内部的分歧,本身也依然是政治哲学问题。施特劳斯为了解决现代性危机,因此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种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构成了现代性“洞穴”的对立。也就是说,古今之争背后依然是哲学与城邦的对峙。
“古今之争”这一洞见,构成了施派学者的基本信条。那么,当洞见成为教条后,如何走出施派“洞穴”,就成为新一代施派学者的重要问题。在施特劳斯的第一代弟子中,就有包括罗蒂、罗森等人明里暗里地反抗;后来,马克·里拉、斯密什等人也与施特劳斯的观点拉开了距离。究其原因,恰恰就在于施特劳斯学派内部本身也存在的“哲学与政治”永恒的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