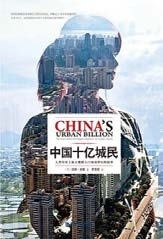改革城乡“二元”政策不应老是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唯有加强顶层设计,痛下决心,才可能在阵痛中新生。
2013年初,中国建设投资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投资蓝皮书:中国投资发展报告(2013)》认为,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70%,城市人口将达到十亿,这也就是说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市和城镇,他们将成为新城民,而这并非一条顺理成章的坦途。翻开美日韩等国城镇化的“老黄历”,均可以找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的痕迹。相较而言,中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是历史大势所趋,同时也具有特色,这就是城乡“二元”政策,还有数十年来围绕这一政策建立的各项社会机制早已盘根错节。
就这一现象,汤姆·米勒在其新著《中国十亿城民》中罗列了诸多现实素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高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造城热,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空荡的“鬼城”开始浮现。
汤姆过于偏重城市现象的写照,实际上,“空洞”现象在许多农村地区同样十分突出。随着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地区难以逆转的潮流,许多村庄仅剩老弱病残,由此导致极其突出的“空村”现象:青壮劳力大量流失、农田抛荒现象严重、乡村治安问题突出、老幼社会保障问题严峻。
一方面是空的村,一方面是空的城,这是极其鲜明的对照。稍加解读不难发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并没有成为城市“光荣”的一员。绝大多数人只能窝居在狭窄、配套设施落后但成本更低廉的城中村。他们在劳动收入、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与城市户籍居民无法相提并论。他们虽然干着工人的活,但只能被贴上“农民工”的标签。他们无法融入城市,也无法回到乡村,怎么看都像是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两端的候鸟——春出冬归。他们在城市里的收入大都比农村高得多,但这种距离障碍也会疏远他们与老家家人的情感交流,这也是大量农民工子女早早抛弃学业,承袭父辈农民工命运的重要根源之一。没有知识不一定就改变不了命运,但其难度系数常会倍增。
突破城乡“二元”户籍政策,这是所有研究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著作均会提及的话题,汤姆显然也关注到这一症结。这也从侧面反映,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已经严重制约新一轮的经济腾飞,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政策瓶颈。取消户籍差别政策是大势所趋,困难在于,数十年来依附在传统户籍政策上的差别化需要更多配套政策解决,除了城乡居民权利的差别化问题,更大的困难在于妥善解决长久以来城乡居民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
户籍改革需要经济支撑,否则大量进城农民将会被坐实在城市底层,形成新的贫民阶层。目前的城镇化,许多城市的主要做法要么倾向于“掐尖”(择优“录取”高学历或高收入农村人口),要么通过农用地变性,实现农村人口户籍身份的转变。如果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彻底崩解,更多农民将进入城市,他们不可能像过去的那些农民那样为城市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换取身份的转变。这也意味着,城市必须为反哺农村作出更多贡献。但时下的政绩评价机制并不能提供有力支撑,很难想象,一座城市会拿出大笔资源,着重解决那些与政绩关系不大但急着进入城市农民的各类问题。许多城市宁愿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GDP,而非用于安置进城农民工。这意味,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破局,不仅要从权利角度进行新的改革,还必须从经济角度作好制度性安排,比如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强进城农民的归属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因城乡“二元”政策暴露的问题早就浮出水面。数年来,围绕这些问题各界均给予过高度关注,也提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建议,比如试验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制度等。倒是觉得,改革城乡“二元”政策不应老是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唯有加强顶层设计,痛下决心,才可能在阵痛中新生。当然,这样极可能影响传统的GDP政绩评价模式,对于那些擅长在GDP上做政绩文章的地方而言,抓什么,怎么抓,如何评价,这或是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