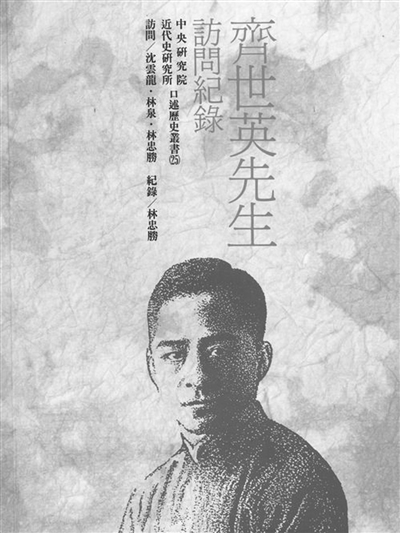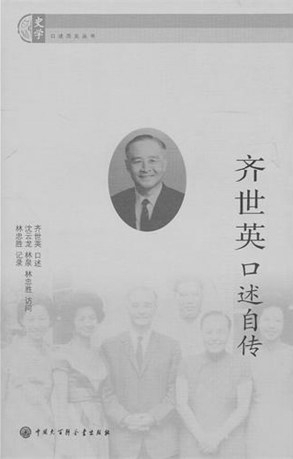去年,齐邦媛的《巨流河》大热后,追根索源,作为书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主角之一——齐父齐世英的生平履历自然引人关注。因此,《齐世英口述自传》更像是对《巨流河》的一种史料性补充。
相较《巨流河》,《齐世英口述自传》严格尊重叙述者口述风格,行文“简单”,语气“肯定”,文风质朴,尤其是间或穿插齐世英的心理想法、及视事处事态度,带领读者一路穿越时空,带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
作为国民党著名党务专家,齐世英的这本口述以相当篇幅,专注于郭松龄将军兵谏张作霖的过程,乃至兵败后不得不藏身于日本新民屯领事馆的那段寂寞的岁月,特别是自己与张学良的诸多纠结。
在齐世英看来,郭兵谏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准备不够充分,把敌方想象得太过软弱,组织乏序,以致本当接近成功时反倒功亏一篑。次要原因则很多,比如郭起兵并没有得到较广泛的民众支持。尽管齐世英没有明言,但看得出,他觉得郭松龄将军过早放弃抵抗,也算得上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巨流河》里可以阅知,齐世英与张学良真正接触并不多,但在东北问题上,这二人却极其重要。从时间上看,二人接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时期,二是西安事变前后,三是在台的最后一次谋面。前面两个阶段,该书均有着重陈述,最后那次,可能因为年老体衰,抑或觉得已然不重要,所以并没有成为该书的重要细节。
在齐世英看来,郭松龄兵谏时期,自己与张学良并无私人恩怨,因为自己跟随郭松龄将军“反的是张作霖”。况且,在齐世英的眼里,当年的张学良年轻气盛,但玩乐过甚,学术不精,难当东北大任。西安事变前,为谁主东北一事,齐世英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并不轻松的角逐。齐世英从所获取的诸多信息判断得出,张学良视自己为惟一竞争对手,甚至认为,这也是张不惜西安事变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很显然,如果顺着齐世英的思路,与我们当前了解到张学良将军的形象,显然格格不入。新中国建国以来,有关张将军形象的刻画,除了英俊帅气,就是爱国、明大义。
那么,在郭松龄兵谏和西安事变这两大历史事件上,张学良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曾出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该书囊括了张学良大半生的经历,尤其对郭松龄、包括后来的西安事变留有较大篇幅,足见这大事件在张学良心目中的份量。
由于所处视角不同,抑或由于各自口述侧重不一,或者刻意回避,在张学良的口述里,郭松龄并非齐世英描绘的那般伟岸。张学良觉得自己同郭私交甚笃,甚至还认为自己对郭的弱点看得比较准,对其“叛变”早有察觉。郭松龄向张学良坦陈自己宁折也不弯,而张学良则表示自己是宁弯也不折。与其说这是二人双方性格的展露,倒不如说是一语双关的暗地交锋。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自认为“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虽然就“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关系,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过较激烈的交锋,但事情的直接起因则在于,张学良不满蒋介石对待学生运动的血腥态度。
到底是张学良,还是齐世英的口述更接近历史真相?即便此二人本着客观的心态陈述历史,但亦难免所处位置差别与局限性,导致结论的差异和欠准确,比如二人对郭松龄将军的评判就大相径庭。
其实,正是由于缺乏严谨的学术式考证,口述历史往往难以逃脱个人有意无意主观意识的纠结,这也许正是口述历史的局限与宿命,即便事实再如何力图客观,但个人评价难脱主观。想想也不难理解,如果评价千篇一律,那口述历史如果没有更不为人知的猛料,必定难以摆脱千人一面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俗套,自然了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