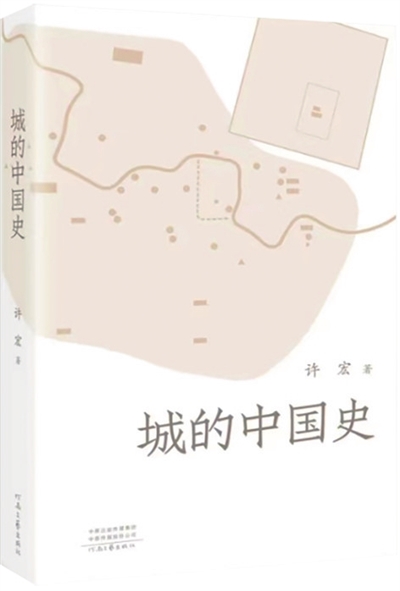关键词 城市 考古 华夏文明
○何毓灵
对于今天的人而言,城市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解释的名词,每个人都能对之产生具象的联想,并且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人事实上已经生活于城市(城镇)之中。因为日常生活于其中,我们往往不会对城市本身过多关注,但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城市”并不是仅仅只是一处居住地——从规划到建设、从个人生活到整体运转,一座城市得以建立、运行离不开居于其中的各行各业人群的共同推动,城市自身有其发展、运行的逻辑,也有其形成、壮大的历史。今天的城市如此,古代的城市亦是如此。
这部摆在读者面前的许宏老师新作《城的中国史》,即是对中国古代城市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探索到成熟历程的研究成果。在书中作者自陈,“要在这几万字的小书中,从‘城’的角度捋出中国古代史宏观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脉络,从城邑和城市考古,升华到对中国‘大历史’的把握与建构。”笔者认为,这句话既是许老师学术关怀的体现,也是该书的题眼,它不仅使考古学超越了狭义“证经补史”的定位,也很好地平衡了简单的“考古学本位”所带来的争论,是读者值得特别留意之处。
作为许宏老师的忠实读者,同时也是一名从事一线田野工作的考古工作者,笔者掩卷之余不仅深受启发,对许老师在写作中的苦心孤诣以及该书的优点与特色,更有着不同于其他读者的认识,以下试从四个方面略述之。
权威性。在公众领域,“二里头”是许宏老师身上最为著名、最具辨识度的标签。许老师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二里头文化研究专家”,但了解他学术成果的人都知道,二里头文化研究仅仅是他治学之一端而已。实际上,许老师博士学位论文所研究的对象正是先秦的城市,该论文在2000年以《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为名首次出版,又于2017年修订增补后以《先秦城邑考古》为名再版。许老师不仅是较早专门从事城市考古的学者,也是长期钻研城市考古的权威专家,他自然是一部“中国城史”最为合适的写作者。
全面性。熟悉许宏老师著作情况的朋友都知道,他曾写过《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一书,这也是许老师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大都无城”概念。与上一本书相比,《城的中国史》以历史的时间轴为线索,由早及晚详细描绘了中国古代城与城市的动态发展史。在这本新作中,作者视野开阔、纵横捭阖,开篇论述“城的前史——无城时代”时并未仅仅局限于中国,而是从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定居地遗址开始讨论,逐步聚焦、过渡到东亚大陆之上。这种在一开始便展露出来的广阔眼光,正预示了该书的第二个特点——全面性。
在之后的章节中,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小型环壕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城池时代的开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邦国时代南方地区的水城、黄淮地区的土城、北方地区的石城,到青铜时代的二里头都邑、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洹南殷墟、周原、丰镐、洛邑,再到东周列国的都邑、城邑,最后进入帝制时代秦汉魏晋隋唐直至宋元明清的都邑、城池,许宏老师高度凝练又细致入微地描绘出了7000余年的中国城市衍生史。这种从眼光到论述的全面性,也反映出许老师在城市考古研究方面的钻研之深、思考之勤。
前沿性。著名学术大家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新学问和新发现都有具体所指,但如果不考虑具体语境,推而广之,则考古学是最适宜展现新发现与新学问关系的学科。对考古学较为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考古学研究的推进十分依赖于考古新发现,许多研究都需要新的发现来证实或者证伪。
不过,与其他绝大多数学科一样,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往往局限于业内而不能及时为公众所知。《城的中国史》一书则很好地弥补了这样的缺憾,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根据参考文献可知,该书所引用材料的最近年份为2023年。毫不夸张地说,读者们完全可以从这部著作中了解中国城市考古的最新发现和最新进展。同时,这也说明在定稿、付印前,许宏老师仍在增补、修改该书内容,这不仅保障了该书的前沿特性,更能体现作者极为认真、负责的态度。
通俗性。作者在书中明言:“这本小书,显然是我在田野考古一线的摸爬滚打和上述或深或浅的研究基础上,试图献给公众的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通识读本。”由此可知,该书的定位明确,是一本普及性质的通俗学术著作。如今,由于图书市场的发展,通史读本、普及著作可称得上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不过,普及性学术著作的写作并不简单,其难度甚至不亚于严肃学术研究。也正因此,具备学术能力和通俗写作能力这两种优点的学者,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笔者看来,许宏老师的普及性写作能力既是天赋,也是多年实践所得。从“博客时代”到“微博时代”,再到今天的“自媒体时代”,自2009年起,许老师已经走过了15年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科普道路。正是有着这份深沉的积淀,许老师才能成为最“出圈”的考古学者,也才能够写出包括《城的中国史》在内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优秀著作。
以上是笔者拜读许宏老师新作后的一点粗浅感想。实际上,无论是书中内容还是该书的出版,都使得笔者产生了诸多思考,留待未来慢慢消化、整理。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优秀通识著作对于读者的作用——这样的作品可以看作一个指示牌、一把钥匙、一份指南,让我们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之下,在继续学习和探索的道路上不至于迷路,甚至能够使得非专业读者(特别是年轻学子)愿意投身于这一学科的专业研究之中。笔者认为,许宏老师通过“辨城”以“著史”的这部《城的中国史》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