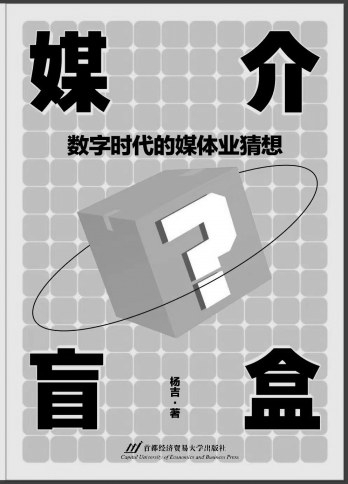■佟周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曾经听一个文学教授聊自己的阅读兴趣,他说自己对社科评论作品的喜好远远大于小说故事,究其原因,是理论评论类文章给他带来强烈的智识愉悦远胜于从故事中获得的审美趣味。对此,我颇有同感,并且个人偏爱阅读言辞犀利睿智的文章,而策划一本评论文集的想法也由来已久。
所以当我看到杨吉教授的书稿内容介绍中有《观念史的书写与顾虑下的叙事》《网络时代,来一场不合时宜的哲学讨论》《数字时代还有“乌合之众”吗》等标题时,不由得感叹这些素材真的很符合我对评论文集的策划设想,这就好像一个对烹饪有虔诚热爱的厨师幸运地挑到了他擅长料理的上等食材。
一道佳肴的可贵不仅在于料理出的美味,更在于其所提供的营养,一本书亦是如此。一本评论文集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其阐述了晦涩的学术理念让人不明觉厉,也不在于其新颖隽永的句式让人拍案叫绝,而是在于评论者基于自己学识与阅历的丰盈对所评内容做的解构与批判。因而评论文集对作者的要求非常高:学识浅薄则无法行在高处,阅历贫瘠则无法洞察世情。杨教授是浙江传媒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创始系主任,同时也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这样的履历背景让我觉得他轻松跨越了成为评论家的门槛。
“以书为媒,从阅读中寻迹媒体业的行进方向与路径”对于这本评论文集的出版目的,杨教授如是说。梳理杨教授的投稿文件夹,他所评论的图书从30多年前对数字时代有无限憧憬的《第三次浪潮》到反映现今媒体融合发展态势的《众媒时代》,从具有学派开创意义的《理解媒介》到预测数字娱乐未来的《网飞传奇》,这些佳作不仅出版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的媒介话题包罗万象。
正是因为作者经年累月地观察与放眼全球的视野,才能对媒体业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轮廓,从而探求媒体业的未来。我按照作者的创作思路厘清了图书的目录大纲,却对作者起的书名“媒体业的数字梦”匪夷所思:“梦”这个字眼怎么可能表达出作者以丰富翔实资料所做的客观构想呢?凭着多年图书策划的经验,我认为这本评论文集的书名一定要改,而且一定要改得寓意深远,否则根本无法承载作者文章中密集的信息量与深刻的内涵。
顺着这个思路拓展,我想到了书中的很多文章都在探讨受到数字化冲击的媒体如何转型突围,如何拥抱Z世代经济。既然书稿里论及众多前沿潮流的话题都意在把控未来,那是否可以称其为“Z世代媒介”,毕竟未来是属于Z世代的,媒体也都在大谈Z世代引导新市场、新经济。但转念又一想,Z世代的表达也有点具象化,这时我又想到了还可以做进一步引申,想到因为Z世代的需求与喜好变幻莫测,形成了让很多人都看不懂的盲盒经济。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中闪现,这本评论集是否可以定名《媒介盲盒》?盲盒不仅是一种在网络社交时代快速崛起的潮玩品类,而且它也蕴含了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有精彩期待。
于是,我鼓足勇气把《媒介盲盒》这个书名推介给杨教授。开始果真如我所料,杨教授对“盲盒”一词与其作品如何链接,不得要领。我认真地给他解释了盲盒的深意,并对他表明:因为书稿所选书评涉及新闻、传播、公关、互联网科技、数字娱乐等多种媒介领域,不同读者读各篇文章后的体悟与获取的灵感又有不同,这何尝不是一种拆盲盒的体验呢?终于我的诚意打动了作者,杨教授对这本评论文集定名为《媒介盲盒》表示认同,并与我见面沟通了他的创作设想与期待。定下书名就为我们编排设计这本评论文集指明了方向:一定要打破沉闷,给读者舒适愉悦的阅读体验。图书从封面到内文都要以市场畅销书的标准来打造,封面设计要加入“盲盒”相关的市场潮流元素。
杨教授长期为《传媒评论》《上海证券报》等媒体撰写书评专栏,发表积攒的文章多达百余篇,但为了突出“盲盒”概念,我们只筛选了其中的68篇收录其中。为了让文集对媒介发展的探索意味更浓,我们又将全书分为上篇“文本·观念”、中篇“标本·案例”和下篇“话本·前沿”三个篇章,以期让读者对媒介观念体系的前世今生一目了然,而对于传统媒体如何完成转型与数字化的革新,作者通过对《大数据云图》《游戏化思维》《众媒时代》等书的点评给了读者多维演进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