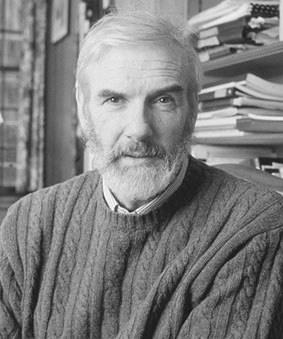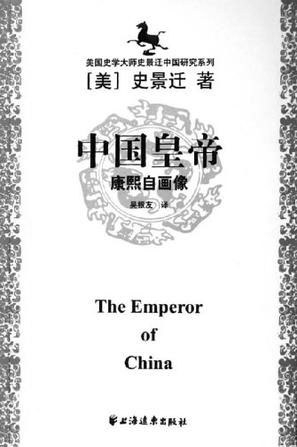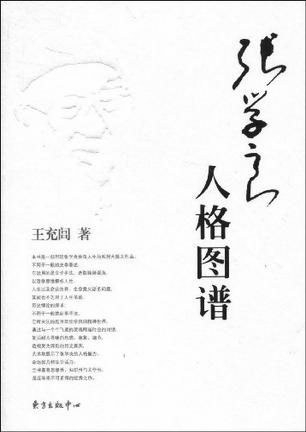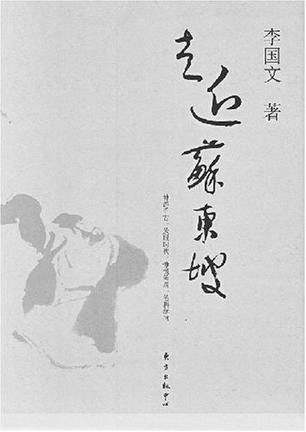○张爱民(东方出版社中心副编审)
传记散文化、散文传记化的文体合流,打破文体畛域之限,彰明了传记散文在当代出版的独特意义。因为结合了传记和散文交互影响的特点,传记散文成为一种具有较高文学品位的文体;传记散文将文化性和历史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也是当今传记写作和出版的新动向。近年来一系列精神高蹈、艺术精致的文本,再次展现了这一文体所包含的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前景,也为传记散文的出版开辟新的空间和可能。本文仅就近年来传记散文的特点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以供出版界及广大读者参考。
曾几何时,传记、散文的写作和出版一度相当的不景气,甚至可以说走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潭。不过,一溪清泉正在不断涌现,那就是20世纪末兴起的传记散文。这个潮流的代表,前有王充闾、卞毓方,后有李国文、梁衡。为了增加作品的形象和直观,以及与读者的亲和力,这些作者毅然走出书斋,亲临历史的现场,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这种传记散文,建立了豪放、大气的话语模式,站在历史的高度来驰骋自己的想象力,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以及文化的追忆缅想,对散落的历史碎片、零星的历史材料进行重新拼构,刻画人物的新脸谱,再铸历史新貌,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这种文体,有人称之为大散文,在我看来,由于它还不能独立于历史人物而存在,与其说是大散文,还不如说是传记散文。正当传记散文作品在华文界掀起阅读热、洛阳纸贵的时候,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史景迁也正以他的教学和作品,深得广大学生和读者的青睐。细心的读者或许明白,《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王氏之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就出于他的笔下。无论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还是连姓名也不知道的乡村妇女王氏,史景迁都平等地将他们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分子,以极大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叙述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
专攻散文的作家把眼光移向人物,专攻历史的学者将笔尖划向传记,凸显出传记散文在当代的出版价值。而传记散文化、散文传记化的文体合流,打破文体畛域之限,则彰明了传记散文在当代出版的独特意义。
文体考察:情感是散文内在规律的惟一逻辑
传记散文是散文长河的支流,是散文百花园中的奇葩,当我们轻舟荡漾于这一脉清流,信步倘佯于这一丛奇葩,我们会发现,传记散文是那么的丰富多彩。
早在先秦时代,传记散文就有了,《左传》(中华书局,2007)、《国策》中有一部分作品记录人物在社会上或政治场合中的言行。只是,正式以传记形式出现的,当首推汉代的《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2013)。从汉代司马迁开始,才有正式用“传记”这一形式来为人作传,记载人物生平事迹,刻划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史记·列传》中,司马迁基本上创立了为王侯将相、高士名流作传的传统。对知名社会人物的歌功颂德或客观评论的传记散文到了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柳宗元以极大的热情去描写普通人,揭示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并以此为参照物揭露社会的丑恶一面。到了现代,则有鲁迅的《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以清新、平易、深情、舒缓的笔调,记述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抒发对亲朋、师友的诚挚怀念,从而成为其中的精品。
关于散文的文体特征,近年来争论不断。有人认为散文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文体,也有人认为散文沦为“文字收容所”,任何不能归入其他文体的文章都可归入散文。的确,在所有文体中散文是最庞杂的,这主要表现在:主题内容无所不包、创作者数量庞大、读者广泛。这样看来,散文确乎会因为没有可视的“边界”而失范,不过,散文有一点是最要紧的,那就是情感因素,或者叫个人生命体验。在小说里,情节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在诗歌里,韵律是构成诗句的规律;而在散文里,情感是构成散文内在规律的惟一逻辑,好的散文给人带来的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交流,是精神对话的享受。散文取材比较自由宽泛,语言优美,侧重抒情,具有文化艺术性。
文本分析:历史与文化的精妙融合
“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史通·六家篇》)作为对人物生平、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等领域的有效记录形式,传记遵循真实性原则,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以达到对人物特征和深层精神的表达和反映。体现真实,丰富翔实,公允评价,选材典型,叙行录言,这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故此,传记侧重对人物的记叙,客观真实是其第一追求。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传记散文尽管也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但是,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爱憎的情感;用文化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从而达到传神的目的。
历史向来是客观公正的,它是怎样子的就永远是怎样的,任何人都不能倒转历史扭转乾坤。然而,人确因其感性思维而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同的人受其情感及阶级立场的影响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就很好地说明了感性思维对人判断力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难逃此束缚。况且,对重大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受当下政治环境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确实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凡人物,都有两个特点:历史性和文化性。在当下的语境下,质疑历史的真实性和本质属性已经不是什么新的话题,真实话语和艺术话语在文本中的交叉使用也极为普遍,当代文学的研究早已表明,所有的文本,即便历史、自传、传记等,也都存在着一些虚构的成分。可见,传记散文将文化性和历史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打破散文和传记之间的界限,是极为大胆的手法,也是当今传记写作和出版的新动向。
作品解读:用散文激活人物用人物滋养散文
中国人写传记散文是有传统的,发展到现在,正可谓人才济济。从近处说,传记散文作家中,既有学养丰厚的中老年作家,也有准备充足的青年作家,最近二十年出版的一批立意、行文新颖,显示沉潜与进取精神的出色篇章,便是很好的证明。比如,卞毓方的“长歌当啸”系列(《十月》)、熊召政的“明朝帝王师”系列(《美文》杂志)、李国文的“透视文人与文学”系列(《文学自由谈》)、梁衡的《大无大有周恩来》(《中华散文》)、耿立的《秋瑾:襟抱谁识?》(《北京文学》)等。
而在传记散文中,最见思想光彩与艺术功力,同时也最能反映这类创作的新探索与新成就的,则是几位实力作家经过较长时间的辛勤笔耕,最终推出的散文专著。它们是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东方出版中心,2009)、李国文的《走近苏东坡》(东方出版中心,2009)、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以及白落梅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等。
王充闾一向主张用散文激活历史人物,同时用历史人物滋养散文。他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亦复如此。只是在既定的价值取向上,这部作品分明寄寓了作家更为独特和高难的艺术追求,他调动散文可以调动的一切表现手段,以不同于一般传记的散点透视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爱国功臣张学良写心。作品在史料的丛林里广征博引,取精用弘,以披露主人公面对历史激流的心理逻辑与人格特征,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命运之谜。
李国文的《走近苏东坡》是其研读苏东坡的诗文及所处时代背景后写出的感悟性文字。作者围绕苏东坡的性格、命运以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深入到苏东坡的精神世界,用洗练的文字,多角度地、十分睿智地为我们描叙了一个鲜活的苏东坡。
经历了十多年的轰动与火爆,传记散文日前渐趋沉稳,这种态势最终将形成创作上的一轮冲刺与喷发,一系列精神高蹈、艺术精致的文本,为传记散文的出版开辟新的空间和可能,也再次展现了这一文体所包含的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