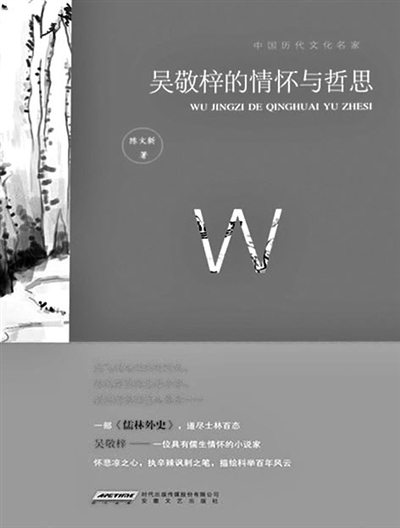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遗留的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远不是对与错、先进与落后这样简单的判断题,对它的评判需要一双能穿越回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别样慧眼——也许在那时,它恰是最为公平的制度,为学而优的士子们打开了进阶的方便之门。
提及吴敬梓,可以条件反射似地联想起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毁掉了吴敬梓,但也成就了吴敬梓。他出身科举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埋首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时文,以求一第。1718年,18岁时进学成为秀才,但此后却屡试不售。直到29岁在滁州参加秀才的科考,终获科考第1名。此后接着参加乡试,又再次失利。1736年,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参加了学院、抚院、督院的三级考试。考试归来后旧病再次发作,未能赴京参加廷试,从此与功名无缘。而他的生活坎坷一如他的科举之路,无善可陈,早年丧母丧父,长期生活穷困而飘忽不定,晚年更是沦落到以书易米之窘境,最后客死异乡。科举是他摆脱生活窘迫的捷径,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是中国传统文人口中的酒和手中的剑。可惜此路不通。在他传世不多的诗作中,时常流露出懊恨与追悔,他无法忘情于科第功名。痛定思痛之下,出身科举世家的吴敬梓似乎醒了,那是一种经历过了,疲了乏了,终于可以放下了的无奈的醒,一部《儒林外史》就这样问世了。
《儒林外史》传世后,各种美誉纷至沓来:中国最辛辣厚重的讽刺小说,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鲁迅先生更是断言:“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面对科举功名,早年的吴敬梓是一个痛苦的失意者,而后期的吴敬梓则是一个冷静的考察者和思索者。正是由于他的醒,他对功名与人品、功名与学问、功名与机缘、功名与世情、功名与风水等的冷静思考与拷问鞭挞,留下了一部以生命铸就的不朽的《儒林外史》,打开了一个真实的清朝读书人的精神世界:意气风发的狷狂儒生,屡试不第的悲凉士子,漠视功名的贤人名士……《儒林外史》以冷峻而幽默的风格展现了科举时代的功名以及围绕求取功名而展开的社会生活。他的描写与记录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科举制度的利弊,深入了解科举时代的民间社会。
吴敬梓之惑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困惑,而吴敬梓之醒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清醒。《吴敬梓的情怀与哲思》一书是武汉大学教授、吴敬梓研究专家陈文新先生的文化随笔集,也是一把试图全面深刻解读吴敬梓的惑与醒的钥匙。全书分别从吴敬梓的生平、小说、文论、交游、儒生情怀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阐释,展现了吴敬梓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贯穿他一生的儒生情怀,更将清朝儒林掰开来揉碎了呈现在读者面前,引人感慨,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