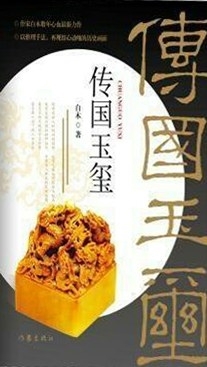用推理的手法,展开历史纪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由传国玉玺的颠沛流离见证一个时代的动荡与辛酸,荣光与屈辱。
○余克礼
作为一名历史系科班出身的学者,当我的目光走完白木70万字的历史推理小说《传国玉玺》,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此刻的心情:欣喜。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两大文化、权力图腾,一个是九鼎,自夏至商及周,凡二千年;另一个就是传国玉玺,自秦至汉、晋、南北朝、隋唐,计一千一百余年。《传国玉玺》截取南北朝后期五十年的风云,开创性地以历史纪实推理的手法,再现一段中国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无法忽略的岁月,读来感佩万千。
作者对正史的实证追求,或者说对历史史实的敬畏、尊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品一直沿着两条主线蔓延,一条是历史脉络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条是传国玉玺迁徙路径的延展,也就是推理主题的故事线的伸展。两条线均是建立在既有正史的基础上。说得具体一点,是以《二十四史》《北史》《资治通鉴》等权威史书记载进行艺术创作的。这中间,至少有三个方面可圈可点:
一是历史的脉络、进程的真实性。如陈庆之北伐,如河阴之变,六镇起义,东西魏五次大战,甚至北周朝局的诡异变迁、北齐帝王们的昏庸腐败,时间、地点、人物都是一丝不苟,严格遵循正史,遵从于既定的历史叙述。
二是历史语境的严肃性。南北朝不同王朝、不同地域的官制、民俗甚至称谓、语言方式,作品都表现得严谨规范。比如宦官,作者没有使用“太监”称谓,“太监”唐朝才出现,本是宦官的首领。就连传国玉玺的保管者,作者都进行了认真考证,启用了“符玺郎”一说。
三是历史场景的实证性。作者曾深入南北朝古战场、历史遗迹实地探寻,比照文字记录,匡正以讹传讹的说法。仅是菩提达摩初来之地华林寺,作者就数度亲临现场。其它如北魏重镇武川、北魏故都盛乐、玉璧古城址甚至红豆传说的发生地顾山,作者都不辞辛苦前往寻访。这些考察,对小说中历史事件的描述和把握,颇有裨益。
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背景、为基础的小说实践。有人说,历史小说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主体是小说,历史则是对主体的限制和修饰。这一定论乍看上去貌似正确,其实不然。既然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描写主题,历史就绝不仅仅是一种修饰和强调。历史的真实度与小说的文学性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近年来,架空、穿越、宫斗之风盛行,一些网络小说甚至大行篡改历史之能事,北齐有名的昏君高湛被塑造成明君,臭名昭著的弄臣陆令萱竟成了励志女青年。个别影视剧,张冠李戴,把历史当笑谈来演义。由“戏说”进而“胡说”,以气死历史学家为己任,把耻辱当光荣,这就未免可悲了。
只有尊重历史方能创造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国玉玺》尤为可贵。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历史本身的尊重。历史小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写法,但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的解构,是需要在对历史吃透的基础上,才能表现的。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作品在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崭新尝试和突破。
历史题材小说走到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且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已经出现一些新的气象、新的变化。白木的《传国玉玺》无疑就是历史题材转折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