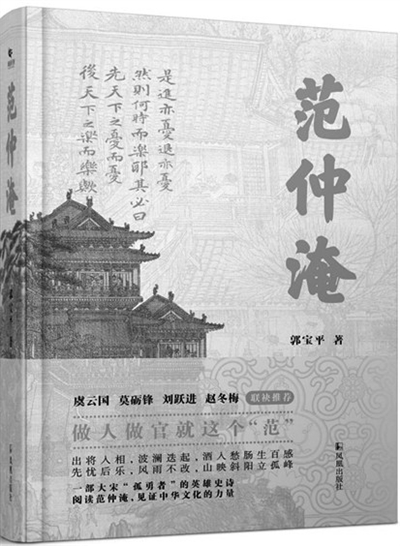○何向阳
郭宝平先生在近两三年内写了200多万字的作品,而且从一位国家机关公务员转为一名专职作家,足见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历史文化进行探讨的激情,也可以看出他写作的勤奋。从成果来看,郭宝平确实步入了创作井喷期。其实历史写作对一个作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甚至高于一般现实题材的创作对一个作家的要求——需要熟悉历史典籍,还要有强有力的文学功底作支撑。郭宝平既有一种客观冷静的历史眼光,又有一种自觉进入历史主体性的文学家把握,因而能创作出这么好的历史小说作品。
郭宝平是有自己历史小说观的人,在《范仲淹》这部书的自序中夫子自道,讲述了他的历史小说观。他说自己的历史小说是将真实性放在第一位,同时也对非黑即白的历史观进行了纠正纠偏,认为历史小说关注的是历史中的生命个体,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这些都是非常辩证的。他对自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决心开创一种历史小说写作新模式——依托历史写小说,以小说笔法写历史,在文学领域为历史书写赢得阵地,在史学领域为历史普及赢得读者。郭宝平的历史小说观是非常明确的,可以概括为三点:还原历史真实、传承文化人格、创新写作方法。
郭宝平的历史小说观其实是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同时也避免了历史娱乐主义。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决定了笔下的历史风云人物的端庄。从宏观来看《范仲淹》,它所呈现的不仅是小说中历史人物的真实样貌,也不仅是作家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和推崇,它更决定着历史在一代代人书写中的传承,决定着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性和纯正性。
作者爬梳文献的功夫和功底,是我想着重谈的。实际田野调查和故纸堆考证,这是历史小说写作的关隘。越过了这个关隘,才能进入历史正殿,一窥其秘密和堂奥。很多人都只是在这个关隘之外,没有穿越关隘的能力。在这一方面郭宝平做到了。他从阅读范仲淹全集入手,也读了当时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的记载,还有后人对范仲淹传记的书写,等等。对于史籍的爬梳和阅读使他获得了与历史对话的可能,同时也使他有能力引领我们穿越历史隧道,领略范仲淹人生,追慕其理想,感受其忧乐,汲取其精神。
另一方面,真正写好一个历史人物、传达一种人格精神,又需要文学上大量的细节作支撑。例如书中的第49章,如没有此章,范仲淹这个人物是不完整的。它写范仲淹离开了宦海中心,到了邓州,建了花洲书院,以兴文运。郭宝平是从作文、做人、做事三个方面来写范仲淹。
首先作文,也就是立言的部分。范仲淹实际并没有去过岳阳楼,《岳阳楼记》是他根据朋友滕宗谅《与范经略求记书》和随函附寄的《洞庭湖秋景图》所写。而写前他还非常犹豫,他对于滕是不是为了博取个人名声而搜刮民财重修岳阳楼,有一点怀疑,直到滕又修书说未动用库银、未敛于民,是债主争相捐资用于重修,而滕在楼成之日凭栏大恸,引起了范仲淹的触动,所以他决定要写,但琢磨如何切入,又拖延了两个月,直至自身经历宦海惊涛骇浪、去国怀乡痛楚,和渔歌互达的美好夹杂而来,才缘情设景,借题引和。所以在春和景明、一碧万顷这样的景物描写之下,我们读到了“微斯人,吾谁与归”这种感怀落笔纸上,写作层次非常细腻,而且递进明显,体现了范仲淹作文的审慎。他由怀疑到信任,然后就借景抒情——当然他面对的是百花洲花洲书院的景,他人生中全部的惊涛骇浪,和在邓州春和景明的景象,两者对比,抒发了情怀,进亦忧退亦忧,写出了文人风骨。该书作者对传统士大夫的感知确实令人敬佩。
其次就是做人。在第49章中,范仲淹对小鬟说,要接一位病人来,在邓州休养,通过药食、针灸等等方式治疗,但还是回天无力。这位病人就是尹洙。实际上范仲淹和尹洙政见并不一致,曾有冲突。范仲淹这样做也有人不解,但范仲淹的回答是:“儒者行事,本就应如此。”这就是传统的儒家情怀。
再次就是做事。书中写道,元昊暴卒之后,范仲淹觉得是一个收复横山的良机,他想上书,但是犹豫再三,还是给韩琦修书一封,提出救弊和攻取横山两事。事情虽然没成,但体现了范仲淹的做事风格,是尽人事尽心力。这体现了一种担当,背后是责任心和使命感,这就是士大夫的责任和使命。
这些细节都体现了范仲淹的文化人格,他在作文、做人、做事各方面都是非常卓越的。这正是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体现。《范仲淹》这本书是一部厚重、立体真实、全面展现范仲淹及其所处历史时代的著作,也完整践行了郭宝平的历史小说观,那就是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者及其杰出人格通过历史小说的书写呈给当代,从而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