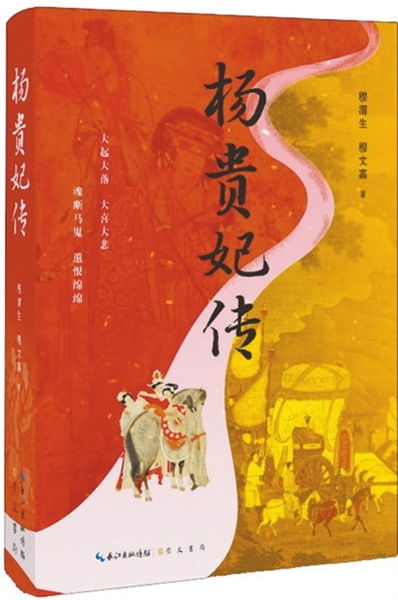○何 丹 徐 辰
杨贵妃38岁而逝,但围绕她的话题3800年也未见得消歇。诚如黄永年先生所云:(杨贵妃)在老百姓心目中始终是个大美人,对她既不敬,也不恨,高高兴兴地给她编点故事演点戏……看样子得继续热闹下去。
今穆渭生教授于崇文书局推出《杨贵妃传》,数十年中,穆渭生教授两度为杨贵妃作传,酌取各家观点,钩沉文献史料,熔古铸今,充实议论,正可谓为黄永年先生之“热闹”平添几分厚重。
“照着讲”
穆渭生教授在自序中即言:“虽圣贤亦不能凭空臆造……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必须坚定不移。”
首先,以正史中可考证史料为主要依据。信手翻检该书,随处可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便是明证。
其次,杂采多元史料以为参照。如论述杨贵妃容颜时,以两《唐书》本传中的记载为主,以《杨太真外传》《开元天宝遗事》《长恨歌传》的描摹为辅,同时借助唐代墓葬、敦煌壁画以及雕塑等其他材料,论证时人乃至唐明皇的审美,综合呈现了唐人眼中的杨贵妃形象。
再次,慎重对待存疑、作伪史料。如杨贵妃故事中,常见梅妃其人其事,真伪难辨。穆渭生教授于“‘争宠者’旧说辩证”一节中,专辟“‘梅妃故事系伪造’”,兼收史论与辨伪之效,且令读者开眼界、广见闻。
最后,以诗歌等文学形式为情感驱动。诗歌常被视为虚构文学体裁,但其承载的感情却是真实而浓烈的,如借杜甫《丽人行》展现杨氏一族显赫与奢华;借唐玄宗《秋景诗》展现开元天子的志得意满;借李益《过马嵬》展现唐玄宗返回长安时,经过杨贵妃坟前的心态与处境;等等。白居易《长恨歌》更是贯穿全书始终,俨然为全书感情基调之注脚。
“接着辨”
对于杨贵妃其人其事,自唐以降,众说纷纭,歧见迭出。而穆渭生教授沉潜唐史多年,卓有成就,全书中多处论点自成一家,颇有学术见地。如在序言中即考证了5个问题、抛出了2个理论:杨贵妃“度道入宫”时间再考定;李唐皇室一再“乱伦”的历史渊源;关于“马嵬事变”的主谋与性质;辨别伪书,指其谬误;注重“制度与习俗文化”叙事;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之异同;讲好真实的“历史人物故事”。以上七点,或涉及杨贵妃阐释史上的热门问题,或关乎历史人物做传的基础理论,穆渭生教授开宗明义,一一予以阐述。其间,新见频出,如:
关于杨贵妃入宫的时间,经清代赵翼及陈寅恪先生考证,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入宫之说,几成定论,不但为学界共识,在社会层面也是广为流传。而此说实出于笔记小说《杨太真外传》,穆渭生教授依托两《唐书》记载,结合寿王夫妇为李宪“服丧”、寿王妃杨玉环生育问题和寿王迎娶新王妃韦氏三件事,推断杨玉环“度道入宫”时间当为天宝三载。
类似的精彩学术考证书中颇多,或深度解析史料,或反驳前人学说,自成一家之言。于学术而言,廓清问题;于普及而言,增广见闻。
“重新释”
其实,穆渭生教授的杨贵妃研究,已横跨30余年,并结成两部杨贵妃传,前者为三秦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唐杨贵妃》,后者为崇文书局2025年推出的《杨贵妃传》。对读者来说,最大的困惑,大约是穆渭生教授两次为杨贵妃作传,《杨贵妃传》与《唐杨贵妃》异同如何?实际上,二书相比,虽有诸多共通之处,不论是文献征引、观点考证,还是写作手法,二者皆不宜以同一书视之,反而可称“合之则双美”。
《唐杨贵妃》引言为“惠妃去后谁伴君”,以时间为序,站在历史宏观角度,阐述杨贵妃入宫事实,堪称平中见奇,引领读者“长驱直入”。
《杨贵妃传》引言为“兴平马嵬杨妃墓”,从旅游者的角度观察杨贵妃死亡、埋葬之地,并将读者拉回到杨贵妃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穿梭于不同时空,而后再展开全书,则如一声叹息,令人回味。
对比可见,穆渭生教授积20年之功,再度为杨贵妃作传,并非单纯的“老书新作”,而是建立在20年来学术界发展、大众认知转移、作者学术与写作观念转移的基础上。
穆渭生教授《杨贵妃传》虽未必道尽李、杨其人其事的复杂内涵,但如其序言所云“讲好真实的‘历史人物故事’”,最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