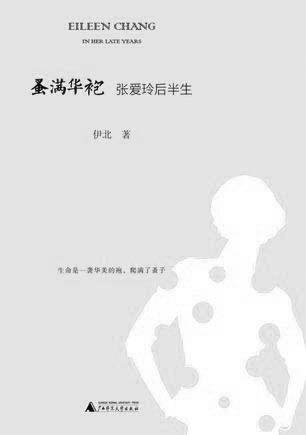无论从哪种视角解读,都无法忽视张爱玲逃离世俗的内心本真。对于世俗,张爱玲其实一直在抗争,只不过用的是一种文字的方式。她也不曾料到,当自己真正在现实中远离世俗的时候,却又无法拒绝精神的世俗。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性!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生!如果把张爱玲的人生倒过来看,兴许她会一直满怀激情。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1943年也即张爱玲23岁时,她在《紫罗兰》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打响。然而经过年轻时的走红后,接下来的便是与饱受苛责的胡兰成结合,再接下来又是远走香港,后又转道美国。本来想在美国打下一片英文写作的天地,结果迟迟难以开花,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与异域过气文人赖雅的结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寻找到了她年轻时的足迹,无奈这个男人年事已高、生活窘迫且病痛连连,能给予她的支持少之又少,索取的反倒多之又多。张爱玲的重新崛起则是赖雅去世后、皇冠社1976年推出《张爱玲全集》(简体字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之后。张爱玲可能自己也未曾料到,促其重回巅峰的不是英语社会,而是母语地区的台湾和香港。
作为一个长期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女性知名作家,张爱玲的文字细腻得有些尖刻,《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中,伊北的文字平缓但充满力量,似乎是对张爱玲那缺乏温暖文字的一种弥补。伊北除了在诸多材料中找寻张爱玲的人生足迹,还读文识人,着力从张爱玲笔下的那些作品中,通过文字构筑的这条幽深小径,走进张爱玲早就将自己圈起来的内心世界。他懂得张爱玲一直是个要强的女性,所以坚决要当面返还母亲的“二两黄金”;知道她渴望通过文字的精雕细琢以便获得读者的认可,除了文字,她没有尝试过别的营生,哪怕生活只能靠淘那些便宜的旧货勉强度日;明白她一直希望寻找到一个可以欣赏激励自己的文人,所以才会有胡兰成和赖雅,哪怕中间横亘着巨大的年龄差距,哪怕最终遍体鳞伤。
伊北的文字,就像是向读者缓缓地讲述一个他所熟识的故人,讲她的写作、她的爱好、她的感情、她的亲情,包括她最痛恨的跳蚤。该书又像是一部温润的人物评传,虽然伊北忍不住流露出许多评述,但又不忍去伤害张爱玲,哪怕可能产生一丝的其它联想。在伊北看来,或是因为未成年前的心灵创伤,看似要强的张爱玲其实最怕伤害。她与亲情的交恶,其实是幼年内心渴望温存的折射。她将亲情一个个自以为巧妙地安插进作品中,然后用文字的方式,让他们一个个接受读者的批判。其实这并非她对别人的主观刻薄,《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中,化身为九莉的她,一样被自己生生地抛向了读者。
晚年的张爱玲,正因为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所以她的生活中才会频频出现跳蚤。虽然文学地位重新回归,无可奈何花落去:她的亲情冰冷,爱情熄灭,虽然她努力在衣食等少数方面保持一些世俗的东西,但仍旧难掩内心深处反感世俗间的那些令她烦不胜烦的“跳蚤”现象。她用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像她后来花上一两百美元购买10瓶特效除蚤药一样,当她试图努力去解决这些烦心事时,但就像是掉进沼泽——越努力陷得越深。她试图以“AA”制来厘清与朋友的关系,结果朋友愈发稀少,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炎樱赴日后感情一路走淡,后来最好的友人(宋淇夫妇)也只能远隔重洋。她与友人尽可能保持着距离,书信成为她与外界沟通最多的桥梁。她曾试图让自己世俗起来,想学习一些理财方面的知识,显而易见,这充其量只是她的转瞬之念。
张爱玲命中注定不是“凡夫俗子”。她的脖子又细又长,她喜欢穿更能彰显东方女性曲线的旗袍,她喜欢拍一些艺术照,但她的那些留世照片总会给人一种冷艳的孤傲。这种孤傲或是她不屑世俗的某种写照。她笃信自己就是为文字而生,无论如何艰难,她都不曾舍弃。她渴望生活在写作的世界,她反感一切与写作无关的纠缠,哪怕付出再昂贵的代价。
因为张爱玲长期将自己封闭于一个逼仄的空间,所以文字是了解张爱玲内心世界的不多路径。在“张爱玲热”中,曾出现过几本同样以张爱玲生平为主旨的传记,如余斌、于青和张均等均曾推出过《张爱玲传》。余斌版的《张爱玲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突出了张爱玲的三重身份,即作家、怪人和异人。前面两个身份还好理解,“异人”显然是余斌独有的解读。“异人”不仅是不同于常人,还是不同于时代,而在伊北的笔下,显然又归结于不甘世俗;于青版的《张爱玲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则突出张爱玲那“苍凉的人生,美丽的作品”。这样最简单的“二元”写照,也是张爱玲外表给人的直观印象。事实上,若刨掉为读者所熟知的曲折人生不谈,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一个“U”形曲线,所以对张爱玲的作品有必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张均版的《张爱玲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版)则是从唯美主义角度去阐释张爱玲,这有点像张爱玲在《传奇》里所写的那样,“在传奇里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找传奇”。张爱玲确有唯美的一面,但鲜为人知的是她支离破碎的背面,包括内心。
这些传记各有千秋,一千个观众眼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张爱玲更是如此。其实,无论从哪种视角解读,都无法忽视张爱玲逃离世俗的内心本真。对于世俗,张爱玲其实一直在抗争,只不过用的是一种文字的方式。她也不曾料到,当自己真正在现实中远离世俗的时候,却又无法拒绝精神的世俗——总有那么几只世俗的“跳蚤”,努力钻进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