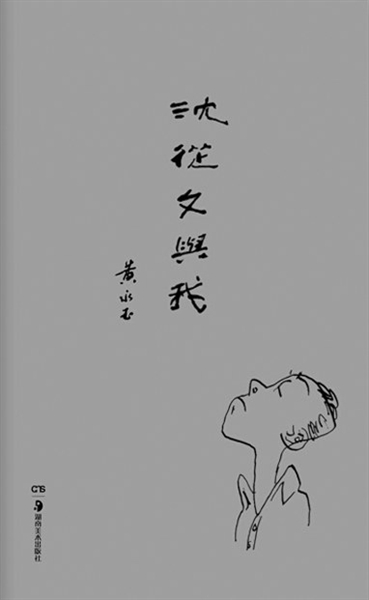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从湘西凤凰走出来的表叔侄,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两人都曾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学圈之外,又都在晚年被逐渐认可。
■李岩(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画家
黄永玉
土家族,画家、作家。1924年8月生,湘西凤凰人。自学美术、文学,以木刻开始艺术创作,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具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套色木刻《阿诗玛》和猫头鹰、荷花等美术作品。从事文学创作70余年,先后出版《永玉六记》《比我老的老头》等作品。
或许是湘西人火爆的性格使然,叔侄二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扮演过“刺头”的角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界言必称抗战的大环境下,沈从文主张“抗战无关论”,认为作家首要任务是搞好创作;1960年代反对个人主义的大环境下,黄永玉又作画加以讽刺。诸如此类的“折腾”行为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历次运动都没能躲过。
好在骨子里不安分的基因,在让他们爱折腾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好身体。沈从文享寿86岁,而今年91岁的黄永玉仍然眼不花腰不弯,不仅记得住80年前小学同学的名字,还能夜里3点爬起来看欧冠决赛。
如今在黄永玉出席的活动中,总能看到一个人的身影。他为黄永玉忙前跑后,张罗大小事宜。这个人叫李辉。李辉当了30多年文化记者,也是出色的散文作家、图书编辑,在多年的交往中与沈从文、黄永玉都结下了深厚的忘年友情。今年,他策划编辑的图书《沈从文与我》出版,书中分别集结了叔侄二人写对方的若干文章。两相对照,自有一番新意。
沈从文后期没写小说是因祸得福
对于沈从文在1950年代后从文学创作改道古代服饰研究,文坛学界历来是惋惜者居多。“如果沈从文一直写小说会有怎样的成就?”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听过很多。
作为沈从文研究专家,李辉在1982年即与他相识。在李辉看来,这一转变对沈从文来讲,并不可惜,反而是因祸得福:“沈从文是有他特定的语言方式和选择人物的方式的,让他写工农兵形象,写革命人物形象,他未必能写好”。
除了写作风格不适应新时代要求之外,沈从文对古代服饰由衷的喜爱,则是他转型的另一大原因:“他本来就喜欢物质文化这些东西。汪曾祺讲过,沈从文早年在昆明的时候,就收藏了很多民间的瓷器、绣品。所以他为什么研究服装呢?他当年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除了有汪曾祺这个“人证”,李辉还有“物证”能够证明沈从文的确从很早就开始收藏古物:“我曾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收了一张沈从文的捐献收据,1952年他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古瓷器卅件,铁瓶一件,漆器一件。本来是他收藏的,他捐给学校了。所以对文物的研究是他早就喜欢的,也不是硬性地让他改变”。
通过临摹《清明上河图》学写小说
黄永玉早年以木刻家身份闯入文坛,此后一手画画,一手写作,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3岁离家的他,一直对老家凤凰的一草一木留恋不已。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几次想把家乡的记忆写成文章。然而最长写到十几万字便放下了。李辉在看到黄老那十几万字的原稿后,力劝他继续写完。
于是从2009年起,85岁高龄的黄永玉开始了他疯狂的写作计划:用小说的形式,把他生命中前四五十年的记忆写出来。要知道他早年的那十几万字,只写到了他的童年。这项写作计划已经过去了6年,如今,这部名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的小说已写完第一部《朱雀城》,三卷共计60万字。如今老人正在以每月1万字的速度撰写第二部,据李辉的估计,2017年应该能够完成。
身为画家,黄永玉写小说是半路出家。然而这也是他能够从绘画的角度思考写作,独辟蹊径。李辉介绍道:“他现在正在临摹《清明上河图》。不是临摹全部,是选局部,在这个过程中体会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倒不是说一定要临摹那个画,他是在临摹的过程中看画里谋篇布局的关系。他是把绘画和文学真正打通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