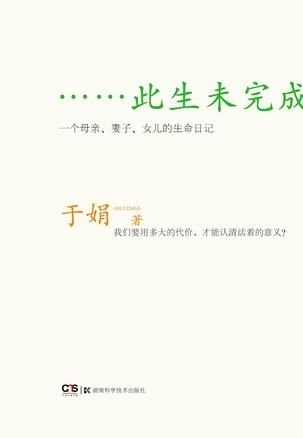前不久,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她的作品在中国面临怪异遭遇:比如《切尔诺贝利的哀鸣》(VoicesfromCher nobyl)被换成新名《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后又换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其实原名应该是《战争的非女性面孔》(War’s UnwomanlyFace);《我还是想你,妈妈: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的原名是《最后的见证者》(LastWitnesses)。(11月9日《西安晚报》)
语不惊人死不休。乍看上去这种书名确实达到了“惊人”目的,但给人的不是惊叹更多的是惊讶。改造后的书名隐约中有种“知音体”的煽情味道;然而,以煽情著称的“知音体”故事,至今尚未发现有作品超越任何一部名著的迹象,尽管这类作品噱头十足,更能吸人眼球。
就事论事地看,《切尔诺贝利的哀鸣》中的“哀鸣”二字显然更能传达一种穿透历史时空的情感意境。《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书名一种被扭曲的人性形象扑面而来更能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最后的见证者》书名虽然通俗,但也传递出作品力图表达平凡中不平凡的深邃思想。相比之下,被改造后的书名虽然表面看可能在第一感觉上更具冲击力,但这种冲击是抛弃原有书名的厚重历史底蕴,是简单迎合通俗口味的“低智”化改造。商业对文学作品的过度侵入,表面上可能促进销售,实际上会破坏文学的完整性。
确实,任何翻译都不是对原文机械地照本宣科,均离不开对原著的必要提炼和再加工。但这种提炼和加工理当尽可能与原文深邃思想保持一致,这也是那些著名译作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有一点我们无法忽视,那就是在译作出版物泛滥的今天,我们依然特别怀念当年那些致力于译作的著名翻译家。这种怀念不仅仅因为历史时期译作的珍稀,更因为一批翻译者的严谨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著名翻译家傅雷译遍巴尔扎克的著作。好友楼适夷特别指出,“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而刚刚过世的翻译家草婴曾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其数十年间在无工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工作。草婴“每翻译一本书,他都会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清楚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然后才开始动笔。在译《战争与和平》时,他还给书中的559个人物各做了一张卡片,注明每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及与其他人的关系等。同时他还会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各方面的书籍,反复推敲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直到满意为止”。还有,草婴每天仅译千余字。这样的“蜗牛速度”确保有充足的时间对字句予以精推细敲,尽可能保证译作的原汁原味,当然也包括书名的严谨。可以说,无论是傅雷还是草婴,其声名成就既得益于渊博学识,更因为他们个人对文学崇拜油然而生的严谨学术作风。
文学规律告诉我们,越是那些抛却表面浮华直抵思想深处内核的作品,越可能穿越历史的旷古时空。换言之,商业当有原则,对文学理当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如果不能坚守,轻易拜倒于庸俗,让文学书香充斥商业的铜臭,最终只会伤害读者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