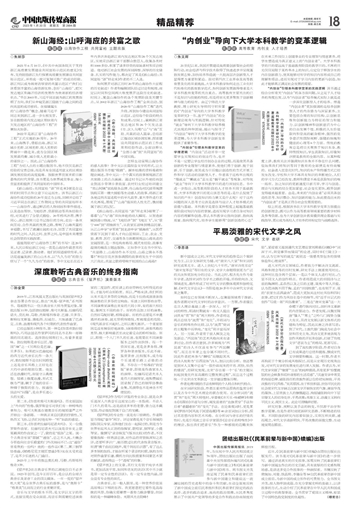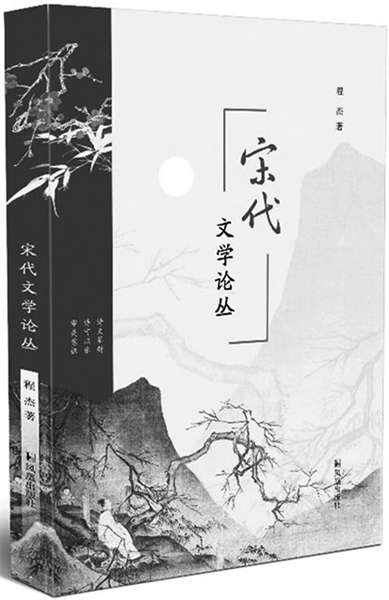○李思语
新中国成立之初,宋代文学研究的趋势是以个案研究为主,以分文体研究为辅,对“唐宋八大家”和宋词的研究成果尤丰。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唐宋诗优劣论”“唐宋变革论”等旧有的文学、史学大命题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加充分的讨论。当此之时,程杰先生作为青年学者,选择宋词作为学术之路的开端,并持续向诗、文领域进发,最终形成了对宋代文学的整体观照和独特见解。《宋代文学论丛》一书即是他20多年中治宋代文学成果之集萃。
如何在已有领域不断深入,在薄弱领域勇于推新,是作者面对宋代文学时的治学意识。一方面,作者擅长在古人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于词的特性,明清时期就有一些文人提出词具有“贯”和“变”两大特性,作者将这两点总结为“流贯”和“变化”,并将词与音乐的特殊性作比较,认为“流贯”使词的主题集中而单纯,“变化”则丰富而深入。另一方面,作者常于前人鲜及之处发新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向来有诸多讨论,但作者注意到,许多被视为“西昆派”的诗人不仅没有参与“西昆酬唱”,而且在年辈上也分属不同时代。因此作者把未参与“酬唱”而继踪其风的诗人统称为“后西昆体”诗人,加以比较分析。他还察觉到宋人文集中总有“一股扑面而来的平易、明快、怡然的情调”,经研究发现,北宋“存在着一个‘乐’的主题从初起到变化终至高潮的完整发展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统一于北宋诗文革新这一文学建设整体历程。
作者处理问题的手法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和时代特点。
在宋词研究阶段,作者注重对作品原典的鉴赏分析以及古今中外艺术理论的联合使用。在分析词的“流贯”和“变化”两大特性时,举姜夔《齐天乐·咏蟋蟀》和柳永《雨霖铃》并逐句分析,阐发前者的“血脉贯穿”手法和后者“愈翻愈妙”的“变化”手法。在论秦观词时,更是累举《梦扬州》《风流子》《望海潮》等40余首词加以分析,探讨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在分析词与音乐的抒情共性时,先是引用波兰音乐学家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中的理论,指出我们把音乐“作为一种感情的范畴来体验”,紧接着又提到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词概》中“词深于兴,则觉事异而情同”的论述,同时举《兰陵王》一词,认为它所写的就是“离别这一情感类型包含的情绪体验和心理境界”。
进入宋代诗文领域后,作者致力于解决诗文流派、风格和理念等的历时发展,研究手法上侧重使用对比,这种对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个体文人进行对比,凸显不同文人的创作特点。作者将范成大的田园诗与之前的陶渊明、孟浩然以及之后的王建、聂夷中等人并提,认为范诗既不同于陶、孟的“田园牧歌”,也有别于王、聂的“农家生活讽谕诗”,范成大更加关注村社风俗和四时农事,把它们作为风俗长卷中的细节,用“近乎日记式的创作”写成一部“风俗漫录”。二是在“唐宋变革”这一大命题下进行纵向对比,剖析诗文革新的内在驱动力。作者发现,汉魏至隋唐“骚人”“寒士”之吟与门阀势力强大有关,其诗文发展以新文体形式的建构为特征,因此汉唐之诗善写悲;到了宋代,士族代替门阀成为社会中坚和历史主角,其诗文更多地表现为创作风格的开拓和创新,打破了传统文学“悲哀为主”的格局,更善写乐。
到了高校教学阶段,作者对自身已有成果进行总结和提炼,撰成宋代文学纲要和概说。这一时期,作者不再拘泥于个案分析或风格探讨,而是从宏观历史视角出发,对宋代文学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发掘。作者认为,宋代文学突破了“缘情”“言志”的纯粹情调,具有更多“纷繁斑驳的社会映象和质朴浓郁的生活质感”,“汉唐文学中常见的绚丽恣肆、铺张扬厉的贵族作派让位给切实细致、平易淡雅的平民风格。”究其原因,在于积贫积弱、世俗平民化的社会使宋代文学缺乏汉唐文学开廓恢宏的气象、雍容华茂的藻饰,上层贵族士人的慷慨超迈、绚丽铺张转向中下层官僚文人的切身处世、平易淡雅;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转向平民主义、现实主义。此论可谓精辟切要。
研究对象、视野以及手法的转变,不仅源于治学和教学需要,也是作者时刻更新研究思路、不断精进的结果。不同阶段的研究内容看似独立,实则互相关联,通而观之,宋代文学清新明快、平易淡雅的面貌完整、生动地呈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