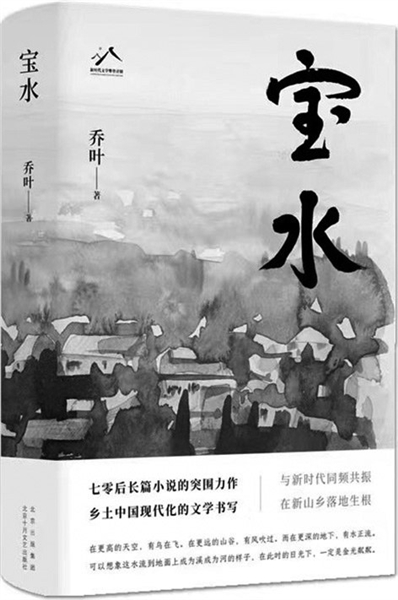■于文舲(人民文学出版社)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得从“农村”谈起,农村是它的核儿。不妨先咬文嚼字一下吧。以前我喜欢用“乡村”替代“农村”,在字典里它们的解释确实差不多,而“乡村”这个词还有一重好处,它与“城市”更有对应性,“城-乡”就像一块磁铁的两极,像两个符号,已经带上了某些文化层面的概括和判断。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农村”。因为《宝水》,我似乎第一次正视这个词。“农”,“农耕”,“农事”,说到底是一种人类活动,这个词里所包含的蓬勃与参差,它具有的动态与变化性,都是因为,它强调的是人,是动作,是人在大地上的创造。相比之下,“乡村”就显得过于静态,过于抒情。《宝水》的质地,是“农村”的。
这“农村”又是新的、当下的,自然就更复杂而不确定。乔叶把无数扑面而来的事物都收纳进小说里——我不是说她没有甄别和选择,但总归是一种“真佛只说家常”的方式,也就难怪我在某篇创作谈中看到乔叶说,《宝水》是她写得最有耐心的一部长篇。但凡缺少耐心也确实很难做到。我欣赏这份耐心,但也有隐忧,因为耐心常常也是挑战,它比较容易造成阅读障碍。如果作家无法让读者充分信任这份耐心的话,就很难把他们带入进去。所以我想在这篇文章里,帮乔叶做一点很可能是画蛇添足的归纳和补充,我就试着简明扼要地谈一谈《宝水》这部小说究竟是在做什么。
在我看来,《宝水》三十几万字其实都在做一件事:为“农村”建立坐标系,从而把当下的农村纳入进去。
小说里的第一套坐标系,是由叙述者“我”建立起来的。“我”,地青萍,是一个农村出身且“懂农村”的城里人,为解决失眠症的困扰来农村长住,顺便帮老原经营村里的民宿。这里天然就带着时间x和空间y2个坐标轴,随着时间的推进,“我”接触农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回到农村,也随时可能再离开,就在两级之间波动。同时,我要强调的是,这里其实还有第三条坐标轴z,就是人的心理,心理认同,情感认同。既然“农村”突出的是人,那么这条最容易被忽略的坐标轴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小说从“我”的视角进入,在整个叙事中,“我”就像一条绵延的丝线,串起散落在农村的人事物。但这条丝线的贯穿,毕竟还是松散的、自然的,有时甚至是不着痕迹的,让你恍惚忘了它的存在。所以《宝水》并不是典型的限知视角,它有全知和宏观的骨架。这里就出现了另一套坐标系,它直接就生成于被叙述的农村。宝水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角,显示出了极大的丰富性。除此之外,往上有九奶的追述,往下有深入农村实习、体验生活的学生。顺着这条时间的x轴看下去,确实是越往当下,城市与农村的空间y轴上的互动就更明显。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里依然有一条隐性的z轴,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标示的是城市与农村的融合。这条z轴也是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就是人所从事的活动。小说中宝水村作为“美丽乡村”的代表,最具特色的就是开发旅游,经营民宿。这是一件立足农村、面向城市的事,既要懂农村,又要懂城市,既要突出农村的特色,又要靠近城市的标准,既扎根在农村的人情社会之中,又有“市场规律”“契约精神”管着,既有农村的性格,又要有城市的渠道,不断建立联系,显然,这是一个平衡。小说就围绕这个平衡点展开,一旦偏离,无论偏向哪方,就是一番波折,一段故事。当小说情节在震荡中无限地接近这条z轴时,当下的农村书写似乎才跳出了“挽歌”模式,体现出它自主发展的生机、力度和可能性。
借助以上这两套坐标系,我们就从时间、空间和人的三个维度走进了小说的内容。而实际上,它的意义结构(形式)也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解析。结构是小说的形式要素之一,其中意义结构相对于布局结构,是一种总体性特征,是由结构形式而体现出的意义。在《宝水》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就是它的章节安排,“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章构成了一个轮回,这是典型的古典乡村的时间观,循环往复,像植物的丰茂与枯萎,确定无疑,没有意外。但读完整部小说,我发现并不尽然。不知乔叶有意还是无意,她在圆满的时间之中打下了一个缺口,一个重要且明显的缺口——春节。春节是中国时间中的一次“大圆满”,为此小说细致地铺排了村民过年前的诸多准备,同时还交代了九奶的喜丧(个人时间的“小圆满”),然而叙述却在春节来临前的最后一刻戛然而止,“我”离开了宝水村,也就是从确定的时间观中跳脱出来,给时间以意外。确定与意外的博弈,或者说平衡,是《宝水》意义结构的核心。空间维度也是如此。表面来看,小说在空间上颇为简单,“来-去”,开头来到村子,结尾离开,这种对称的、偶数拍的、相反相成的行动轨迹,也是拒绝意外的。但另一方面,从现代小说的结构方式来看,《宝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这个离开,并不是最终结果,不是结论,而是一个新的问题的起点,这就把一个“正-反”的结构变成了“正-反-未知”。最后,在人的维度上,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两部分的人,构成了人物形象,构成了命运,构成了当下的农村。
读完整部小说,可以感到,乔叶试图确立当下农村的热情和野心是明显的。而我这里也就是帮她画了几条辅助线。文学当然不可能像计算题一样精确,纳入了坐标系的新农村是否真能标示为某一个点,本来也不是小说家的必答题。甚至结论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忽然想起张柠先生有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小说家是努力把脑袋探进世界的人,评论家(理论家)是试图把世界都装进脑袋的人。这么一比,就显出后者的疯狂了——特别是在面对最鲜活的当下时。现在就让我的这份疯狂适可而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