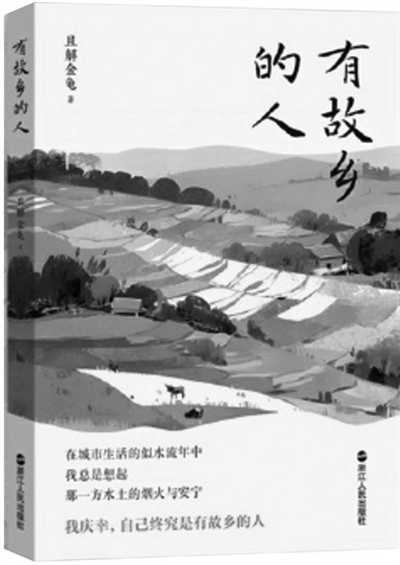○高明勇
阅读胡森林的新著《有故乡的人》,适逢农历春节,又恰好去了浙江绍兴。
特别的时空,不免想到鲁迅那篇著名的《故乡》,“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故乡”也好,“乡愁”也罢,其实都算是人类表达的母题之一,但凡作家,这几乎是绕不开的文学选题,中国作家里,“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的“故乡”书写,都已成经典。
漫步在绍兴街头,鲁迅故居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最著名景区,鲁迅已成为故乡的“代言人”,文章中的名言,也都被做成文创,随处可见,做成标语,贴在墙上。
对于漂泊异乡的人,对于背井离乡的人,“故乡”都是极为复杂的存在,特别是对于那些“逃离”故乡的人,故乡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诗意栖居,很多能用心感受的东西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中提到,“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更是引起多少人的共鸣。学者陈平原表示很喜欢这种“态度”,他认为,如何谈论“故乡”,这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心境”。
从作者现居城市北京,到《有故乡的人》中提到的湖南衡阳,相隔1600多公里,其中篇什写作时间持续20多年,相对于鲁迅的心底“清醒”以及笔底悲凉,在100年后重思“故乡”的时候,作者有着别样的“心境”,他感叹“庆幸”,“自己终究是有故乡的人”。
我在鲁迅的故乡,白天闲逛,晚上读想,发现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谁才是“有故乡的人”?
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属于那片土地。冬去春来,容颜不改,无非改变区划,改变名称。临近终点却又无法抵达的“隐山”,恍若诗情画意又升腾烟火气的“墟集”,故乡的雪,故乡的雨,故乡的星空,都仿若是一种游子的寓言,故乡熟悉而又陌生,抽象而又具体。
物理意义上的故乡,属于那些乡亲。物是人非,缓慢流淌,或徒增华发,或消失在故乡的土地。在鲁迅的笔下,这是闰土、孔乙己、祥林嫂、阿Q的故乡。在作者笔下,这是父辈的故乡,他着重记录了自己的父亲,“建了大半辈子房子”的勤劳父亲,“从不占别人一点便宜”的厚道父亲,“上学不多,但很有文化”,“有时间就读书看报,到每个地方都要探访那里的乡土风俗和民间逸事”的好学父亲,“在阳台上砌上花园,植上牡丹,在屋前垒上花圃,种上桂树。四周种上各色花草果树,让这里四季瓜果不断、鲜花飘香”的浪漫父亲,“一辈子在乡村,不乏粗粝的生活中,却惊异地保持了灵魂的高贵”的优雅父亲。
心理意义上的故乡,属于那种乡愁。弥漫人世间的,经常是那种“亲人在,故乡是春节,亲人不在,清明是故乡”的苦楚,那种“记忆无时不在,寄托无处安放”的茫然,那种深夜在异乡街头的一声叹息。
然而,作者没有满足于这种地理意义的探寻,物理意义的记录,心理意义的觉醒。他写“故土难忘”,发现的是“人生如逆旅”,远看是漫游,近看是回乡;他写“湖湘形胜”,关注的是从湖湘山水中孕育出的那些胸怀“千秋事业”的乡贤,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蔡锷等;他写“乡愁袅袅”,却清醒地认识到,“乡村成了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他者,而仅仅是怀念的对象、表达爱心的空间和被改造客体”。
故乡之所以成为人类表达的母题之一,在于“人的存在”必然会面对时空切换,而不同的时空观也对应着不同的“心境”,我在《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中写过,一个人,如果一直待在故乡,无所谓思念不思念,故乡就是日常,日常的往往也是最容易习焉不察,最容易无视和忽视的。一个人,一旦离开了故土,远离了乡音,并且年岁日增,漂泊感越强,对故乡的思念才会更加醇厚,不管是否愿意承认,他都会有意无意地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
就像作者所追问的那样:这到底是重回旧梦的一厢情愿,还是停留在记忆线上的刻舟求剑?如果进一步追问,谁才是真正“有故乡的人”?如何才能做一个“有故乡的人”?“有故乡”之后呢?
他之所以称自己是“有故乡的人”,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不断思索,找到了与故乡的“连接点”,接下来,他还会不断追问,寻找与故乡的“距离感”,不断记录,寻找与故乡的“契合度”。
(作者单位:政邦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