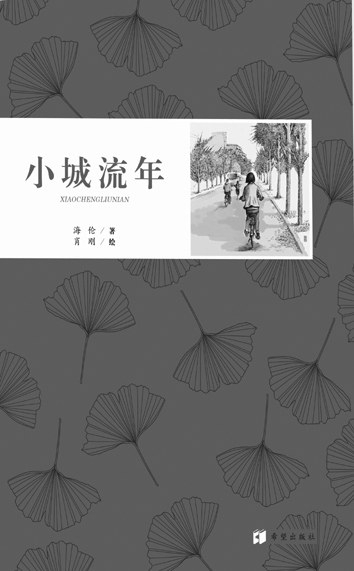这不仅是一部情意缱绻的童年之书,也是一部文笔俊美的文学之书,更是一部用恬淡的散文笔调书写的童年回忆录。
冰心老人写过这样的诗句:“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小城流年》是一本自传体的成长小说,也是一本用恬淡的散文笔调书写的童年回忆录。有对渐渐远去的童年往事的回望,有对依依飘散的小巷弦歌的追寻,也有对曾经走过自己生命的亲人、邻居、少年伙伴的感念与怀想……透过温暖、细腻和清丽的文笔,童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边边角角,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个人色彩,化作了一种足以引起人人共鸣、带有永恒和普遍意味的文学主题。这就是作家笔下的童年之美,也是《小城流年》所呈现的文学之美。
童年的梦影里,有多少欢欣,又有多少乡愁。面对流逝的往事,即使是最坚强的心,也会变得呜咽。回望者将从中认出,有微小的一部分是属于她的,还在那里完好地保存着,而那庞大的部分,却不再为她所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拥有了。正如作家在书中写到的那样:小院的瓜架绿叶还在,童年的蝉声也依稀可闻,但是,那个趴在夏日窗台上听着蝉叫、等着妈妈回家的小女孩,却不知不觉地长大了。
《小城流年》讲述了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等最敬爱的亲人的故事,也讲述了孔阿姨、梁老师、小黄叔叔、小雅阿姨、王校长、玉儿哥哥等等难忘的邻居,以及众多童年伙伴、少年同学的故事。这些都是走过了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人。可以说,《小城流年》就是一本《雪人》式的作品,也是一本《城南旧事》和《呼兰河传》式的作品。如果再扩大一点范围,那么,这本童年之书和萨特的《童年回忆》、本雅明的《驼背小人》、托马斯·曼的《童年杂忆》、柯莱特的《葡萄卷须》、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呈现的也都是一样的况味、一样的文心。
推开童年记忆的窗户,多少被尘封在那里的最细微的体验和最真切的感受,都像被掩藏在温暖地窖里的青嫩的葡萄藤,只等早春的微风吹来,它们瞬间就会返青和发芽。作家那童年灵光闪现的文字,就是这样一捆瞬间返青和发芽的葡萄藤。每一串细小的童年故事,都是一丝生机无限的葡萄卷须。
法国作家都德曾经这样描写过他童年的感受和体验:“小时候的我,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我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可以进去。”读《小城流年》,我仿佛也感觉到了一种童年记忆和童年感觉的全部打开。故园月明,酒旗风暖;庭下新枣,堂前旧燕;青梅竹马,深巷弦歌;放学路上,承欢膝下……女作家把槐花树下的小童年,写得何其丰盈、恣意,何其鲜活、灵动。
黄昏时分,妈妈在巷口呼唤孩子回家加衣裳、吃晚饭的声音,是那么悠长悦耳;槐花盛开的季节,孩子们攀爬到老槐树上,采摘洁白、清甜的槐花的身影,依然历历在目;还有妈妈要出国时,“我”和弟弟搀扶着年老的姥姥,站在家门口送别的时刻,能不让人潸然泪下?……回想着父母堂前、姥姥膝下的幸福时光,回望着爸爸回家、亲人相聚,邻里之间、真情怡怡的那些日子,作家自问自答:故乡是什么?故乡就是成长的回眸。这也真是应和了罗兰·巴特那个著名的观点:只有童年,才是家乡。
诗人兰波有言:所谓诗人,就是看谁能够回到童年的一种人。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更应如此。童话家林格伦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够给我以灵感,那就是童年时代的我自己……‘那个孩子’活在我的心灵中,一直活到今天。”在《小城流年》里,那个名叫“小青子”的小女孩,也像从来没有长大的彼得·潘一样,一直生活在女作家海伦的心灵里,只要轻轻一声呼唤,她就会带着满身的槐花香,踩着银杏路上金色的落叶,奔跑而来,笑语朗朗,活灵活现。而这时候,童年的一切将重临心头,宛如昨天。
有位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大人物的回忆是属于“历史”的,小人物的回忆是属于“文学”的。此言虽非定论,却有一定道理。《小城流年》是一本情意缱绻的童年之书,也是一本文笔俊美的文学之书。作者海伦虽然是英文翻译专业出身,却有着深厚的汉语文学、尤其是中国传统古典诗词素养,这在她的字里行间不难体验。可是,在享受了该书带来的童年之美和文学之美之后,我也不禁生此感慨:生活的节奏真的太快了,时间都去哪儿了?你们看,连70后这一代人,这么快都在开始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