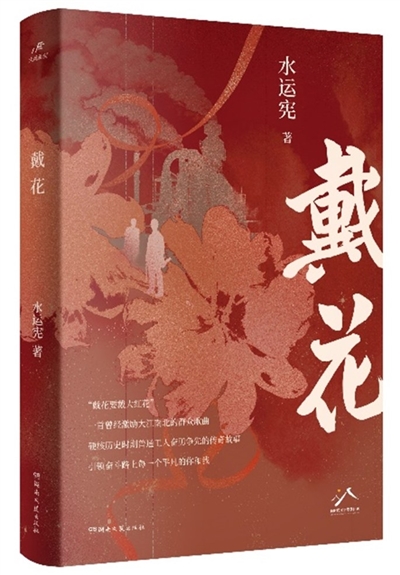中南大学原创文学读书会本期围绕水运宪最新长篇小说《戴花》进行细读。这部工业题材小说以工厂车间为原点,勾勒出血肉丰满的日常细节,由小见大,还原20世纪60年代末现实与精神层面的立体图景。身为时代亲历者的作家将其情感与体悟付诸笔端,一句“戴花要戴大红花”,延伸出特殊历史年代对于实现个体价值的精神追求及其传承脉络。大红花象征着奋进争先的生命底色,这既是时代的遥想亦是精神富裕的赞歌与回响,诸多思辨浑然融于对特殊物件与底层人物的关注中。小说尤重刻画包括女性角色在内的各色人物,在生动的对话间交织出带有典型特征的鲜活形象,铺设出繁复错综的关系网络,颇具节奏感与戏剧性。(晏杰雄)
刘希:以诗意化理想反抗价值失落
《戴花》围绕以杨哲民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和以莫正强为代表的工人展开,讲述他们在德华电机制造工厂为同一个劳模梦想接力奋斗的热血故事。《戴花》将笔墨集中于莫正强不顾一切争当劳动模范的过程:年轻时一穷二白的莫师傅为了造出冲天炉“起码折损了十年阳寿”,最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他患上严重的矽肺病离世。小说将莫师傅对待职业的理想信念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原本可以转去浦陵纺机厂,得到更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但回忆起在电机厂投入的心血便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在自己屋里”;在国庆假期期间,他为了保障熔炉设备的安全,无偿住在工厂守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硬撑着从病床转到熔炉班工作一线主持庄严的开炉仪式。他用最后的气力发出了“点火”的命令,既点燃了熔炉之火,更是用崇高理想点燃了人们的生命之火。
“写什么”表面上是关于题材选择的问题,实际上却隐含着作者的历史认知。从萨特的观点来看:“人要完全成为人,不能靠返求于自己,而在于自身之外寻求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才恰恰是解放、体现自己的东西。”“戴花”对于莫正强而言,劳动模范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更是优秀无产阶级工人的精神表征和自身劳动价值的最高认可。如果把他追求“戴花”的历程看作一段朝圣之旅,那么他在旅途中收获到的是充实的内心和强大的灵魂,是老骥伏枥般的壮志豪情。
水运宪在《戴花》中用虔诚浇灌出感人肺腑的劳模故事,着重塑造以莫正强为代表的劳动模范,通过将青春乃至生命奉献给国家事业的人物演绎出生命的英雄维度,形成了独特的小说诗学品格。水运宪可谓是以文学形态抗拒价值失落的重要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文艺方向标。
吴翌名:宏大叙事的当代书写范式
在《戴花》中,水运宪坚持他一贯对于人性的关注,给出在宏大叙事下挖掘人性之泉的独特范式,即书写平民英雄的悲剧色彩。
小说这样描述主人公莫师傅解决“堵铁水”失误的情形:“亡命地堵住了出水口”,“我师傅前步弓后步冲的样子,像一尊油光黑亮的铜雕,顶在那里纹丝不动”。莫师傅技艺高超、舍身为公的形象成了一尊“雕塑”,英雄的光环闪耀周身,这无疑是一种传统的英雄化的记叙。不同点在于,这一情节之前是对莫师傅迷信思想的书写,他居然相信“神水”可以包治百病,这又离传统叙事里完美的英雄形象相距甚远。在《戴花》中,作者为诸多人物设计过英雄的瞬间,与之相应的是避免人物走上神坛的努力。人物的英雄光环是一次性的,翻过某一具体情节,这些人物又变为了普通人。作家选择为人物增添一抹悲剧性色彩,用生命消逝的悲壮感托举起人性的光辉,进而将人性中积极的一面定格。
在小说后半段,作为老一辈炉工的莫师傅深刻感受到徒弟的创新对自身地位的威胁。作家为莫师傅安排的退场方式则是对于悲剧意味的十足放大:莫师傅因经年工作患上矽肺病,时日无多。莫师傅在退场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举动,他肯定了徒弟的创新改造,并将评选劳模的机会“让”给徒弟。这都是对他之前形象的颠覆,同时也意味着私欲的消除,这时候的莫师傅近乎是一个完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诱发观众情感的方式在于使比观众自身好的人无故遭难。这恰与水运宪的情节安排相匹配,在小说的结尾,象征劳模身份的大红花被放在了莫师傅的坟头。这是对莫师傅平民英雄地位的确立,也是对其真善美的人性的最终定格。
曹晏萌:回溯中人性光环与阴影的现实观照
水运宪的《戴花》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限知视角,并以“固定式内聚焦”为主要叙述方式。小说借主人公杨哲民之眼,讲述特殊历史时期下工人阶级苦中作乐的生活以及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气魄。
小说以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叙述眼光直接呈现了“我”进入电机厂后的心理状态,并通过一系列的对话与内心剖白,建立了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主观精神空间。在小说中莫正强形象的塑造就是在杨哲民,即“我”的眼光观照下完成的:“说实在话,这人给我的第一印象简直糟糕透顶。用一句文明话形容,那叫乏善可陈。”这是“我”与莫师傅的初见,他的形象是粗陋难看、胸无点墨的。随着情节的推进,“我”对莫师傅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我”第一次到师傅家做客后发出感慨,“他内心的激情已经把我烤热了”。伴随着生产的开展,莫正强逐渐表现出高超的专业技能,流露出对炼炉事业的热爱、对劳模梦想的执着。这一步步地打动着“我”,师傅的形象也在一步步拔高。“他舍得性命,那才叫绝技。师傅把炉子看得比命还重要,那是一个人的本质。其他的优秀都是学来的,本质的优秀是天生的。”至此,“我”对莫正强的态度完成了从最初的怀疑、厌恶,到敬佩、感动,再到最后将其视为楷模的转变。
这个过程是借助“我”和莫正强之间的关系变化来完成的。“身为人物的叙述者所能获得的信息量决定于他们的时空位置。”因而“我”和读者一样,与莫正强在空间上和心理上始终保持着距离。这一距离随着“我”的叙述逐渐缩短,读者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认识人物。甚至可以说,“我”的情感变化与读者的阅读和想象是同步进行的,这就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也更加具有张力。
张雨怡:时代书写下缝合式的生命串接
《戴花》是湖南作家水运宪立足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一部作品。在作者笔下,“戴花”的含义与深嵌于时代的“劳模精神”被树立在同一水平线上。小说将情动个体放置在广阔而本然的生活现实中,通过小人物升降浮沉和日常琐屑生活的开掘,探寻人性的幽微之处,开发作为审美体系的真善美在当代社会的更高价值。
作者表面上采取了一种较为平淡的叙事模式,即以时间的流驶为表层线索。但实际上,波澜不惊的时间外壳下隐埋着主人公波折反复的心理走向。《戴花》借杨哲民之口,叙述与莫师傅有关的情节,在施以旁观者目光的同时实现了自我的体认与省悟,达到一种“缝合式”的治愈和升华效用。小说中,“我”(杨哲民)从一开始觉得师傅“拿不出手”,到后来深切怀念师傅的高风亮节与忠于职守,经历了一个曲线上升的过程。其中,“我”对师傅的情感变化并不是单一向度的,而是绵密悠长、反复多变的。杨哲民接过莫师傅的大红花意味着接过师傅对于熔炉班的殷殷期盼,那是汇聚莫师傅全部心血与气力的产物,是其坚韧不拔的劳模精神在生命层面的最高象征。在师傅最后的指挥和诀别中,“我”也意识到“劳模”的真正含义,接续了无形却有重量的精神境界,秉持着与师傅相同的信念,身体力行地诠释着新与旧的生命串接工程。至此,创新与守旧的固定概念被解构,并由感人的精神承续重新统一起来,为小说引入了一股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劳模精神的追求和实践依旧是如今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戴花》立足于时代又超越时代,其中所蕴含的生命串接意识值得每个人深度追问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