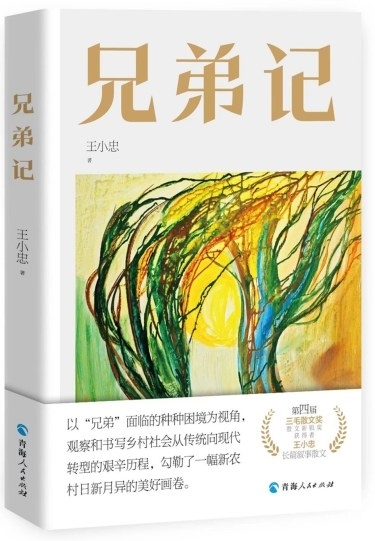○卢顽梅
读王小忠长篇散文《兄弟记》,多次潸然泪下。《兄弟记》上篇从兄弟关系入手,看似写兄弟间的家长里短,却并不局限于兄弟关系,而是从兄弟间的交往与情感纠葛延伸至农村与城镇的书写,通过兄弟关系的演变,展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给甘南农牧区接合地带来的巨大变化。
故乡村风逐渐变坏是从农民外出打工开始的,随之而来的是田地与村庄的荒芜,而田地与村庄的荒芜带来人心的荒芜。外出打工刺激了农民对金钱的欲望,农民种地的本分被追求富裕的雄心彻底抛弃,一夜暴富是他们的终极梦想。“兄弟”这一原本十分温暖的词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日渐冰凉,人与人相处的根基已经动摇。
王小忠敏锐地洞察到,兄弟们如何被社会发展的滔滔洪流裹挟着前进而自身不明。对金钱的极度渴望与非理性的消费致使民风恶俗,村子失去了固有的朴素,享乐与奢靡占了上风。乡村民风的恶俗,礼仪与伦理道德的溃败,主要表现在婚丧嫁娶等方面。几十年前村里办丧事,是很神圣、很隆重的集体活动;而今,办丧事成了衡量一个家庭是否有经济实力的标准,也变成家人是否尽了孝道的重要参考。过去的婚姻习俗是父母按照门当户对的标准为子女择偶,由于村子里相对贫困,娶媳妇花不了太多钱;可现在,娶媳妇越来越难,婚嫁的排场、天价的彩礼往往使一个并不富裕的农家陷入困境——七拼八凑好不容易凑齐了彩礼,换来的未必是安宁的生活,很可能遭遇背离,鸡飞蛋打。同样,农村流传千年的走亲戚礼仪也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团拜”。团拜更讲究形式与场面,缺少认同与关爱,让人与人的关系、村庄与村庄的关系变得松动,加速了农村社会心理结构的瓦解,导致了人情的凉薄。
王小忠通过梳理兄弟间微妙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向我们展示了农村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如何一步步迈向了溃败的边缘。在探究农村衰败的原因时,王小忠敏锐地捕捉到人的本性——人身体里有一种可怕的甚至罔顾法纪的欲望,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的本性并非追求平等,而是寻求差异——总想活得比别人更好。正是贪求享受的欲望给人带来痛苦,带来恶行,而人又很难战胜自己的欲望。
父亲对兄弟们所经历的一切,有着透彻的看法:“人一辈子要经历很多苦难,比起大街上讨饭的苦命人,你们还有啥抱怨!”在父亲看来,守住田地是作为农民的本分,可兄弟们似乎很难领悟父亲的深意。
王小忠在展现农村社会变迁的同时指出了兄弟们自身的弱点——心眼小、狭隘、贪小便宜、好面子、斤斤计较、精于算计、缺乏反思、缺乏节制等等。兄弟关系就是这个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缩影,王小忠通过兄弟关系的变化映射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迁,正如作家所言:“中国的农村,无论天南地北,情况大致如此。”然而,无论兄弟间有怎样的恩怨,却终究做不到彻底的分裂与独立,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
《兄弟记》下篇通过讲述胡林生、李福与“我”在少年时代结拜兄弟,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各自流散的故事,流露出深深的无奈感。中年的入世、无奈跃然纸上。作家感叹光阴的无情,人生的艰辛、无奈与沉重。
《兄弟记》补篇中,王小忠追溯了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的半生纠葛,既有特别年代引发出的人性邪恶和仇恨,亦有人世间的诸多荒唐事,对于父辈的历史,作家更多的是理解与释然。
牟宗三曾说:“……唯有游离,才能怀乡。而要怀乡,也必是其生活范围内,尚有足以起怀的情愫。自己方面先有起怀的情愫,则可以时时与客观方面相感通、相粘贴,而客观方面始有可怀处。虽一草一木,亦足兴情。”虽然游离于故乡之外,王小忠对故乡怀有深厚、复杂的感情。《兄弟记》记录了王小忠对故乡、对兄弟的赤子之情,是他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故乡已然回不去了,但王小忠用文字镌刻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历程,写出了生命中难以言说的疼痛与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