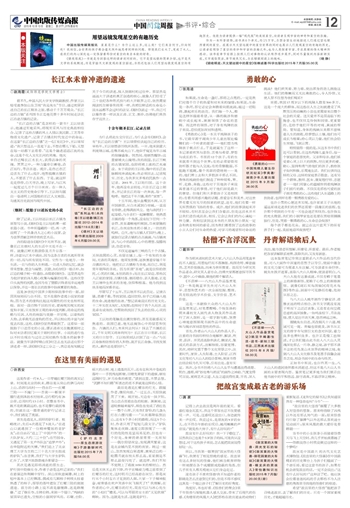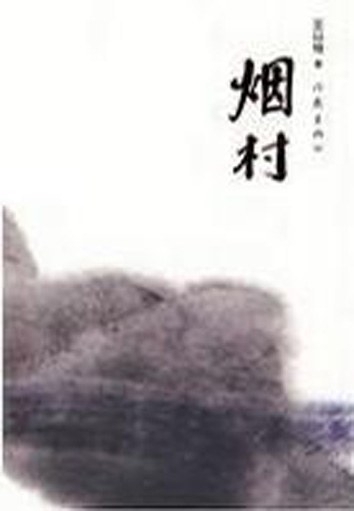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作家王以培受邀参加山东卫视“我是先生”节目,通过荧屏讲述自己的长江朝圣之旅,感动千千万万观众。“长江边的古镇”系列图书正是他花费十多年时间走访长江沿途古镇的记录。
“长江边的古镇”是怎样的一套书?王以培表示,他通过实地采风,将现实采风与历史典故相结合,记录了这些古镇的风土人情以及民歌、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了古镇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在这套“长江边的古镇”之一《江有汜》中,王以培写道:“我只想这么一直走下去,不想在哪儿下船,又想在每一站都下去看看。”这是个融进滔滔江流的生命,这是个化入文化长河的灵魂。他庆幸自己喝长江水长大,获得洁净的灵魂。冥冥之中,一种力量牵引着他,沿江而行,寻访古迹。或许,是自己在江边丢失了什么;或许,他想提醒古镇的人,不要丢了什么东西。于是,就这样走走停停,白天寻访,晚上写字,与江风一起度过几万个日日夜夜。在一种人文主义的历史使命引导下,王以培勾画出一卷清明上河图般的长江人文地图,勾连其历史故国与现代中国。
《烟村》:脱胎于口述历史的小说
除了记录,王以培还以长江古镇为原型写小说,《烟村》是王以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中所蕴藏的一切,再一次说明了一个具备诗人之心的小说家,会为世界贡献怎样珍贵的艺术品。
诗的踪迹在《烟村》中无所不在,就像长江在烟村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一样。就像江畔无数晨昏及月升日落一样,诗意从江水中涌出,因为这条古老的水流所带来的一切,而与所有别处不同。它作为一处地方、一种生活,一旦与你的人生相遇,一旦进入你的记忆,就会带来想象、想念与痛楚。民歌,如《诗经》一般古朴,如江边的橘子树一样通俗,点缀着《烟村》。这显然是作为批评家的诗人精心收集与编纂的结果。这些仅靠口头流传的民歌,也因为有了慧眼识珠者而幸运地得以保存,并在一部长长的故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是20世纪中国多少部相似故事中的一部,却因其结局而与众不同。它不是剧作者或小说家的虚构,因为艺术的虚构比起这戏剧性的历史也相形见绌。面对一段百转千回的历史,要再现其现实的深度和丰富,只有放弃主观的单向度判断,将命运的残酷与反讽、人性的病弱与美德一并呈现。以虚构的人物,去承载无法虚构的历史,并以相应的丰富与深度去匹敌,这些,《烟村》显然都做到了。这看似一部脱胎于口述历史的小说,谭正清弟兄在搬离烟村之际对来访者回忆着关于烟村的往事。小说的进行也以不时在现在与过往之间切换作为基本的叙事手法。就像当年读《呼啸山庄》时怎么也无法适应那个讲述者一样,读《烟村》过三分之一,我总是匆匆跳过关于今日的讲述,投入到烟村的过往中。那显然是远远大于讲述的真正创造的核心,就像人们经受了二十世纪各种形式技巧的大开眼界之后,依然需要阅读托尔斯泰和雨果一样,我相信鲜活的生命是小说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法宝。《烟村》读过一半,我已可以像作者一样谈及正清、正艾、善珍,仿佛他们果然存于这世上。
十余年朝圣长江,记录古镇
为什么将此生交付长江,为什么会有《烟村》,会有“长江边的古镇”?王以培曾经谈起自己的经历。早些年,王以培曾游历欧洲各国。一日,他来到意大利庞培古城,在维苏威火山下,他似乎窥见当年古城的煊赫盛象。恍然间,他顿然醒悟:这里曾被火山掩埋;我的故园,长江三峡的古镇家园,也即将被上涨的江水淹没。生于南京的王以培,胸中的长江血脉瞬间奔涌起来:我必须回去,记录现实、历史,为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作一点记录。2001年,王以培归国。这十余年,他再没有去别处,只在长江边上朝圣,并记录长江的每一次奔流,每一声咆哮。他把这千年古镇,称作“家里”。
十五年间,他从鱼嘴到木洞,从万州到新田,从白水溪到白帝城,一直没有停歇,走得满面风尘。他与渔民们一起登船,与乡亲们一起睡棚屋。他熟悉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没有拉下任何一个音符,甚至清晰地听闻到,日夜驱驰的长江,在夜凉如水的小镇上,一丝丝的呜咽。白天,他与古镇人们同行;晚上,就独自记录古镇的点点滴滴,与古镇夜谈,与心中的故园,心中的理想,促膝而谈,仿若亲邻。
不仅足迹遍布三峡的几十个古镇,关怀故园的心灵,也留在镇上,每一个有知的生命间,无语的灵魂里。他须发依稀,还挟裹着穿越千年古镇的风尘。他把长江古镇称为圣地,而自己,则是常年朝拜的圣徒。因为所谓“圣地”,就是信仰的依托,心灵的归属,永恒的故乡;而在长江岸边,那些沉入江底的家园、古镇村落、烟雨楼台、亲人墓地,正是王以培毕生所求的圣地、信仰和根基。他为找到这块圣地而深感幸运。
尽管写了十五年,王以培并不以此自足。记录古镇,思接千载,寻找家园,追回信仰,似乎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流进他的血液。“想记录淹没区的历史文化,十二年实在太匆忙,太短暂;但相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是卓有成效的,它帮助我找回了失去的信仰,心灵的家园。”
王以培的笔触是出离忧郁的,甚至是敏感而又焦虑的。故园已逝,他无法掩饰心中的留恋和忧伤。古镇的人们,未来何去何从?抹去了古镇的长江,千年文明又将奔向何方?长江在日日常新,长江又将日日坚守。王以培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与长江命脉相依相存的人和物,离开长江命脉,寻找发展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