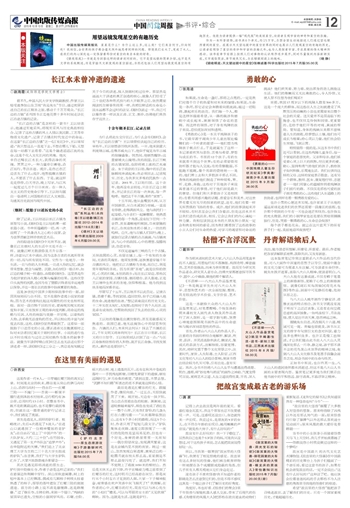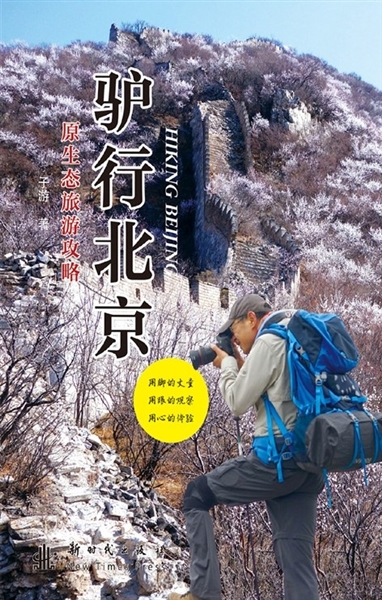这是作者一行8人,一日穿越红螺三险的真实记录。时间是北京的秋末,路径是从房山的驷马沟村上山,沿泗马沟村——自由石——红螺三险——不掩门——杏黄——断崖羊圈行进到涞沥水村结束,总行程约有26公里,总用时约13小时。在整本书中,既不是距离最远的,也不是攀行最困难的,但就在这一篇普通的驴行记录之中,我们遇见了美丽。
首先是遇见人,同样的驴行者。粗略统计,先后6次遇见了5波人:“在进山口就遇到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驴友”;在自由石“追上了‘中国户外’的一大队驴友,大约二三十位”;在竹园寺,又遇见了另一支户外队伍“追梦户外”;在中险附近的天梯,“我们追上了北京理工大学为主的二三十名大学生组成的驴队”;在杏黄,我们“与大学生驴队汇合了,大家兴致勃勃地合影留念……
其次是遇见即将消逝的原生态。驴行到中险极乐寺,作者子游是这样记录的:“我们在悬崖边和荆棘中穿行。深山里秋意阑珊,树上的枯叶基本上已经飘落,偶或有几颗柿子树枝头挂着熟透了的柿子,厚厚的落叶遮住了红螺三险的斑斑遗迹。前方的小路上说不清是藤缠路、还是路缠藤。” 过了极乐寺,左转右转,来到一个垭口。“残缺的屋顶早已遗失,空框的小窗洞穿风雨。石碾、台阶、硕大的古树、地上遗落的瓦片,还有在秋风中卷起的落叶……手抚残垣断壁,目睹先辈留下的遗痕,顿有远隔时空、岁月沧桑的感觉。”读到这里,不禁去想,“沉醉不知归路”所表达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心情。
最后是遇见红螺谷的灯光。跟随作者,继续向前,“一过五点,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刚开始,天边有一抹夕阳,为山峦点亮着血色的轮廓。渐渐地,这道轮廓越来越窄,颜色也变成了酒红色……整个山里,只有我们驴队的几盏头灯在山腰闪着……”从夜幕降临到出山,还有5个多小时的路程,而这5个小时,作者只用了短短几段文字:“驴队集体走夜路,速度立即放缓了……夜行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有一个好处,身旁的悬崖常常一无所知……偶尔仰望夜空,发现满天繁星,这是北京城内见不到的夜景。转过一座山,忽然发现白里透黄、黄里泛白的一轮圆月就在枝头那么高,星星倒是不那么晶莹闪亮了。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爬上了海拔1050米的棺材山。然后是无休无止的下降,终于在精疲力竭之前看到了红螺谷的灯光,这时明月已经高悬在夜空。那是夜行五个小时左右才见到的人烟,大家一下子精神振奋,疲劳感在欢声笑语中灰飞烟灭了!” 我理解,在作者的心中,红螺谷的灯光,简直可以与冰心先生的“小桔灯”媲美,可以与邓丽君女士的“又见炊烟”辉映。因为,这就是生活,这就是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