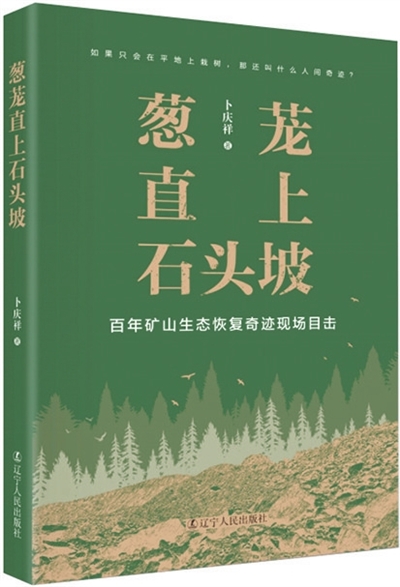关键词 田野调查 鞍钢工人 集体主义
○张 浩
以一种极其老派的调查方式和文笔,卜庆祥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20万字新作《葱茏直上石头坡》,却令人惊讶地展现出了某种对于后工业时代书写的突破性质。其虽以自然生态的恢复为主题,但其中所混合着的时空坐标、阶级风景、地域文化以及共产主义理想,都昭示着这部作品绝不能草率地被划归为文学自然主义的范畴。因为当我们注意到书中描绘的工人群体再一次成为集体意志的“急先锋”,实际上也就不得不承认鞍钢充当了“工业中国”向“生态中国”转换的那个轴点。换句话说,这个“绿色寓言”的生发之处隐匿着属于同一传统却是不同时代的对话,而正是通过这种具有再开拓意义的“复归”,我们才得以窥伺到一种意义不止于当下现实的中国式生态美学正在开枝散叶。这种生态美学承接着自近代便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想象的一贯命题,以理想主义高扬时代的精神气质作为底色,以儒道文化中的古典思想作为补充,重新放置了自然结构中人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位置,并在这个过程中指向了某种触手可及的有形未来。
为《葱茏直上石头坡》积累资料的过程可称漫长,长期的田野调查这种几近失传的技艺在此展示出了其独特的辐辏感。正是基于作者卜庆祥3个月的实地考察,书中第一人称视角的移位和深厚的笔力都极具分享性质,它慷慨地提供了一个述、评、忆结合的全息式的观察方式,个体、集体、自然、历史在此都不再失语。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考察方式和写作态度下,我们才得以深入到这场绿色复兴运动的肌理之中,发现存在其中微妙复杂的褶皱。这正是《葱茏直上石头坡》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的成功之处,亦即其始终秉持着一种作为人文研究应有之义的实地考察精神。因为非虚构作品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先天带着对于田野调查的亲近。只有进入到具体鲜活的场域中去,发生才可以不止于发生,而是上升为一种发现,使最终付梓的文字不止于成为一种感情淡薄的冷眼旁观。从最终呈现的结果来看,卜庆祥显然已经完全地进入到了那个场域之中,当他沉浸其中,也就过滤掉了来自于外部世界的那些繁杂的情感,变得更加专注,“发现”也就随之发生。
而在这场“发现”之旅中,令人惊喜的恐怕不只是那些重返葱茏的石头坡。更重要的是,就如同70多年前诞生于鞍山的那个有关钢铁的奇迹一样,现在这个绿色奇迹的引领者,依然是来自于鞍钢的工人们。这又在另一个角度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其中还存在着某些有关理想和精神更为厚重和宏大的隐喻。
《葱茏直上石头坡》通过记录鞍钢工人为修复生态环境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读者勾勒出了共和国最新一代工人的生动形象。这些描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一穷二白的艰苦环境下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第一代工人。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卜庆祥用文字对一个又一个绿化队的普通工人进行了摄影机式的记录,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们是如此接近新中国伊始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工人阶级形象,以至于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似乎就在此交叠的感受。而这些鞍钢工人在书中的集体亮相实际上是在相当程度上纾解了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乡愁,因为当作者将这些工人集体的劳动场景呈现在阅读者面前时,随之发生的是共和国历史上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的复归。书中写到的绿化分公司经理马德生曾这样回忆工作时的场景:
“就像大会战一样,工程24小时不停,四周拉上电线,拧上灯泡,不分黑天白夜地打点、钉桩、放线、挖坑、栽树……大伙的决心大,干劲大,那场景,过去好多年了都忘不了。”
一种单纯而珍贵的情感就在马德生的追述中微微颤动——“就像大会战一样”,“过去许多年都忘不了”——这是一种与共和国历史发生的奇妙共鸣,因为工人阶级的光荣时代亦是集体主义理想高扬的时代,马德生在当下看到了历史,亦从历史看到了集体主义完成复归后的未来。《葱茏直上石头坡》这部作品的珍贵之处亦在于此,作为一部非虚构的作品,其虽饱含“复归”式的情感,但却没有指向漫漶的哀伤,它展示给它的读者:作为集体主义思想最为坚定的继承者,作为辉煌历史曾经的书写者,鞍钢工人有勇气也有能力重新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近些年来,以老藤、津子围等人为代表的东北作家们似乎开始更加乐于去展示东北地区的新形象。而作为这次书写潮流的一员,《葱茏直上石头坡》在此成功地将生态恢复、时代精神、民族理想、个体价值整合为了一个有机体,展示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气质。它指向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民族文明传统,从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出发,将人间问题作为一切灵感的源头,保持着思想上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使得对于新时代中国大陆历史实践的记录免于成为象牙塔之中者一念之间的产物,最终完成了对于现世中国的积极肯定。而这种对于四方中正的和谐美感的追求又具有如此广阔的外延性,它或许昭示着一种内涵更加丰富、世界观更具价值、思想更具感染力的中国式生态美学正在逐渐生成,因而也就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