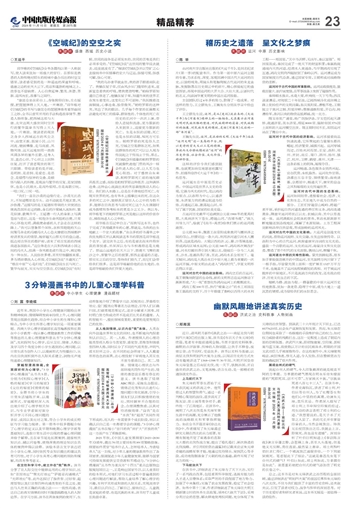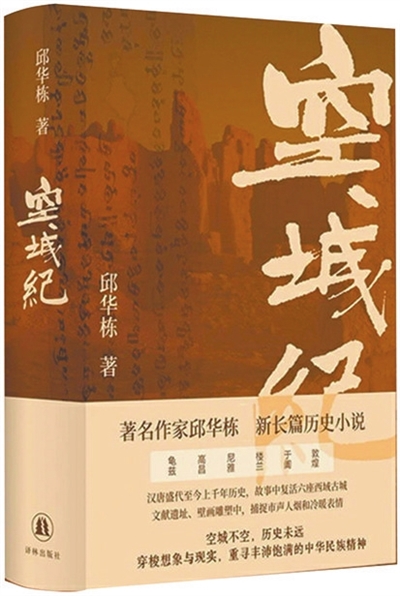关键词 盛唐 西域 历史小说
○王运平
邱华栋的《空城纪》全书各篇均以第一人称叙写,使人读来犹如一场盛大的穿行。在那似是熟悉的人物和绝对陌生的场域中叠合而出的时空交错里,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遥远的深邃和呼唤。盛唐之边的长天大云下,荒凉和蓬勃的地域之上,故事也不曾缺席。人心自我延伸、繁茂、休憩、革新、迎风而长,故事与之同行。
“康昆仑坐在彩台上,身体俯仰自如,左右摇摆,把琵琶弹得上天入地,一片琳琅。”邱华栋对《空城纪》的书写与康昆仑的琵琶弹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全书以虚实并用的手法构造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把西域这部与大唐、北宋这两大盛世同时空并行的繁华篇章书写得上天入地,一片琳琅。使读者的现世之身步入西域远古的风尘之中,庙堂王族、低屋小民、山川河流、壁画佛像、走马商旅、风物风情、远天远地如同一曲曲风调各异的塞外长歌,过身入耳、直达心田,于心田之上回环往复,打开了读者观世的第三只眼睛。带给读者的是开阔、是明朗、是悲悯、是爱恋、是思念、是错愕与惊异的交叠、是顿悟与陷入的纠缠、是荒凉与繁华的反复、是家国情怀,也是小民烟火,是浅吟低唱,亦是高歌引吭。一唱三叹,三叹一唱。
“我们一直在沙漠的边缘行走。沙漠无比浩大,不知道哪里是尽头。动不动就是天地玄黄,风沙弥漫。”这描写的是王延德所带领的大宋使团出使高昌国所走过的路,身后的汴梁城人流如织、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王延德一行人的身影上写满苍凉与悲壮,这是一场饱含生命风险的出使,只有内心怀抱光明、满载使命感的人才会走在这样的路上。“我可以想象那个深秋,在积雪皑皑的天山间策马奔走的冯嫽冯夫人心急火燎前往西域都护府请求发兵的情景,她穿越天山那无尽的盘山道,抵达郑吉所在的都护府,请来了郑吉发派的西域南道各国救兵。”这位奔走在大汉和西域诸小国之间的冯夫人,挂满一身风霜走进竹简之中,被定格为一种永恒。人说俗世多艰,其实仔细翻拣来看,多为琐碎磨洗人心所致。《空城纪》说“不避死亡”“根在中原”“心是归处”。《空城纪》说生长与死亡、繁华与寂灭、实实与空空俱在。《空城纪》说“有时候,世间的战争是必须发生的,世间的苦难是我们必须承受的。”《空城纪》说“这世间的繁华说去就去,说没就没有了。”细读《空城纪》并以空旷之心去接纳书中所描摹的宏大与辽远,俗情可缓,俗惑可解,俗心可寄。
“我的乌孙妻早就去世,我的孩子跟着商队走了。我躺在屋子里,任由风沙从门缝里吹进来,逐渐窒息着我的呼吸,使我使劲咳嗽。”帕特罗耶知道自己很老了,他躺在屋子里,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这变化已不可逆转。“我抚摸着这面铜镜,心事沧桑,脸带微笑。”帕特罗耶的这种笑,笑出了我的眼泪。几乎每个作家的长篇都无法避免对死亡的描摹,群体性的、个体性的死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次次上演,带给人悲恸和洗涤,更为簇新的人来到世上,迎接更为簇新的死亡。生是永恒的话题,死亡也是永恒的话题,知死方可乐生。帕特罗耶的死是俗人之死,空城之空是群体之死,如果说群体性的死亡可以让人视为传说起之于传而止于传,那么,《空城纪》所描摹的帕特罗耶的死就像吹进他门里的风沙一样会吹进人的心里,让人无力也无心阻挡。对于盛世众生来讲,帕特罗耶死亡前的境况颇具孤苦之感,而恰是帕特罗耶这种孤苦、这种满怀沧桑、这种由心流淌出来的笑容最能拨动人的心弦。我们的人生路上,总是在不停地经历死亡,有现实世界的死,也有书本上描摹出来的死,在这众多的死亡之中,能够真正留在人心之中的为数不多,能够在自我思考与面对死亡这个人生课题时成为救赎和参考标本的更是少之又少。我以为,邱华栋笔下的帕特罗耶之死是能以这样的价值存在,被收纳进人心之中的。
邱华栋在后记中自言:“而我写这本书,也终于完成了我埋藏多年的心愿,那就是,为我的出生地献上一个宏大的故事。”在众多的好书清单之中我优先购买并认真阅读这本书的原因是邱华栋这个名字。读完该书之后,有的是望名而来终得所获的喜悦感,并深深以为与书相遇得还是太晚了。那远山远地的长天大云下、那漫天飞舞的黄沙之中,那繁华之后的寂寥,那西去遥遥的古道,那实实之后的空空,等待我们很久了,而它们会带给我们很多。这是邱华栋献给他的出生地的,也是邱华栋献给我们华夏大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