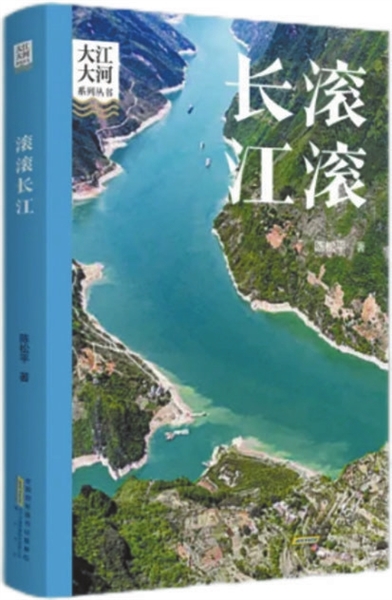○陈 璨
陈松平的最新作品《滚滚长江》不同于一般的以长江为主题的科普读物,它以长江为载体,探究其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千姿百态的一面,丰富和拓展了长江的精神内涵。作者陈松平描写长江时,既强调源头的意义,又关注每一条支流分布在不同地理形态下的差异化特征。正如陈松平所说:“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在陈松平的文字世界,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追溯长江根与脉的直接工具,他以雄浑、刚健的笔力,梳理出一条江水在百转千回状态下最真实与鲜活的一面。
书名《滚滚长江》,“滚滚”二字呈现出一种波澜壮阔之感,充分地概括出长江的壮丽磅礴,给读者内心以深深的激荡。
探究长江,寻根溯源,沿着作者陈松平的文字,我们去一睹长江的容姿。从遥远的唐古拉山脉主峰西南侧的各拉丹冬雪山姜根迪如冰川出发,遥望巨大的冰凌在阳光照射下,焕发成一滴滴水珠,在地上汇聚成缓缓的水流后向东海之滨奔涌前进的壮观景象。经历亿万年的封冻期,上游段长江如脱缰的野马,争先恐后奔向大地,布网织线,勾连山川;又如康巴汉子,在川藏高原的尽头吹响雄浑的赞歌。陈松平的文字极富诗意,构建中游段长江的文字处处张扬着诗性与对美的向往。“百里画廊”“天然博物馆”等赋予长江浪漫的色彩,而“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等诗文又填充了这种浪漫之下的实在内容,在景与诗的相互加持中,他带我们探见了云谲波诡之下长江最温柔的一面。循着陈松平的文字一路南下,长江从巍巍高山峡谷抵达缓和广袤的平原,奔腾的身姿愈发轻盈与舒缓,真正做到了超然灵动、旷达自适。而入海之际的长江,携带着万里长途上具有不同天性的3600多条大小支流从吴淞口跃入浩瀚东海,自此,波澜壮阔的万里行程走到终点。陈松平笔下的长江具有一定的意识性,从初始阶段的自由恣意切换到温柔浪漫的状态,历经万重波澜,最后显示出完全的洒脱自在,它能够自然而然地与天地融为一体,主动适应着生存环境,揭示最真实的自我。
在《万里巨川》一节,陈松平借助诗歌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具有诗意色彩的、宏大邈远的长江画卷。一组与地理空间相对应的诗歌,恰好中和了自然地理题材作品中语言的极致理性化与直接化,使笔触更加温柔、细腻。比如,上游的山高谷深、流急凶险是杜甫笔下的“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中游沃野千里、湖山相连的景象是李白笔下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下游的江阔渺远、水天一色是文天祥笔下的“一叶漂摇扬子江,白云尽处是苏洋。”陈松平在构建文字内容时,追求一种“画面感写作”,他借助诗歌语言来表现现实环境,以诗歌语言的独特视角探寻长江的内部肌理、外在状态。
《滚滚长江》在回溯长江一名的由来时,紧贴史实,从历史的时间线中挖掘并逐步确定“江”的概念。《寻踪觅源》一节首先提到,早在春秋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直指这条百折向东的万里长川为“江”,并以史料逐步佐证,讲到《诗经·周南·汉广》记载:“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里的“江”亦指今日的长江。随着“江”的概念逐步清晰,探索更加深入,展现其源远流长地理特征的“长”字和表现其磅礴壮阔气势的“大”字相继出现在“江”字之前,二者结合,成为固定名词。时代车轮滚滚向前,“长江”一词出现在三国和晋代的文献典籍中,并成为与战争紧密关联的地理坐标,有《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的“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也有《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的王羲之致信向殷浩建言:“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随后,长江又被晕染上浪漫的色彩,这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诗歌蓬勃发展,不少诗人开始借长江抒怀言志、寄托绵绵情意或是慨叹人生,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千古名句,广泛涌现。
《滚滚长江》在考证长江的若干别名时,关注到与其相关的地理、历史、商业发展等多种因素。如“通天河”,其所在河段海拔高,常年裹挟在缭绕的云雾中,恍若从空中倾泻而下的一条通天之河;巴塘河口至四川宜宾市岷江口一段,称“泸水”,究其名之由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宋代时,从巴塘河口到岷江口,资源丰富,盛产沙金,因而又被称为“金沙江”,沿用至今。
在陈松平洋洋洒洒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江于历史的时空隧道中不断地演化,并被充实着新的内涵。俯仰古今,回到历史深处的长江,在波澜之中,寻觅它千姿百态的模样。无论是沱沱河,还是楚玛尔河,抑或是当曲、扬子江、浔阳江……它们都共同拥有一个名字——长江,它们如片片星羽分布在北纬30度的每个角落,在斗转星移、云奔潮涌中共同书写奔流不息的理想与追求。